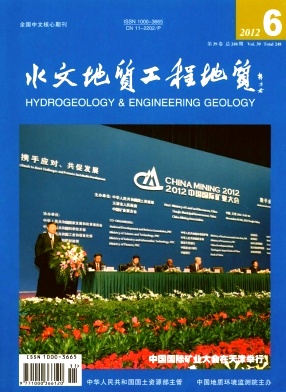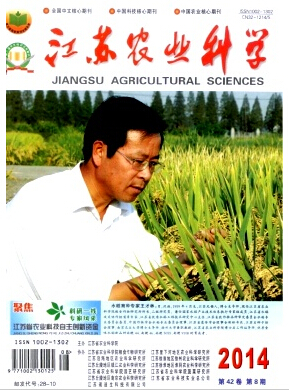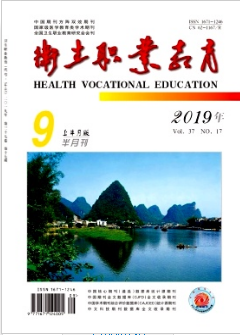乾嘉扬州戏剧中心城市确立原因探析

摘 要:乾嘉时期,扬州之所以成为江南地区戏剧中心城市乃至花部重镇,首先原因在于扬州作为移民城市对于多元文化象征的花部剧种的包容与接纳。其次,以扬州学派为代表的学术流派以融通、客观、科学的进步思想洗涤着统治阶层宣扬的腐朽伦理道德,为花部兴盛扫清了道路。最后,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改变了以往以士人审美趣味为主导的社会审美风尚。最终在扬州剧坛上形成了以“瓜棚柳下”的花部为主导的俗世审美潮流,也确立了清中叶扬州作为江南戏剧中心城市的地位。
关键词:扬州戏剧中心;花部;移民文化;市民阶层
中国戏剧,自宋金杂剧以来,每个戏剧样式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城市进行着自身的发展。在由宋到清的朝代鼎革这一历史进程之中,“中国戏剧大体经历了12世纪宋杂剧、金院本的形成,13世纪元杂剧和南戏的创生,16世纪明代传奇的新举,18世纪清代‘花雅之争’中‘雅部’向‘花部’转向等先后四次戏剧审美范式的变革”[1]。在这四次审美范式的变革之中,每次戏剧样式的转变也都伴随着戏剧中心阵地的地理转移与空间变化。且在每次戏剧审美范式的变迁之中,戏剧艺术中心的地点并不是唯一的,确立中心地位的时间也不是与朝代更迭时间同步的。

如果以北宋时期的汴梁算中国戏剧第一个艺术中心的话,宋金对峙时期的温州作为南戏艺术发展的策源之地,元代以大都作为杂剧繁盛的核心城市,南宋的杭州则是宋金杂剧的演出重镇,传奇则是以明代中叶时期的苏州作为全国戏剧的主盟之地,清代中叶则是以北京和扬州南北双城作为花部和雅部戏剧的竞胜舞台。虽然这种叙述略显笼统,但大致能勾勒出各个时期戏剧艺术的聚焦之点。在中国戏剧样式的盛衰过程之中,戏剧艺术的中心城市也在发生着地理意义上的转移。这种地理位置的转移之于戏剧艺术而言,对戏剧史的梳理,文化史的书写,甚至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建构,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戏剧艺术的发展史,更是地域文化、社会族群之间审美争胜与交融的反应堆。
清代的扬州作为百种戏剧艺术的交汇之城,为戏剧的多样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扬州于乾隆年间成为南方的戏曲中心。”[2]而在它之前,苏州一直作为江南甚至是全国戏曲的中心存在,扬州是如何战胜苏州,并取代其地位的呢?
按照《中国戏曲通史》中所论,扬州之所以成为南方的戏曲中心,是因为交通便利,漕运频繁,商业发达,大盐商集中,具有非常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还因为弘历皇帝几次南巡,两淮盐务为着御前承应,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把很多各种地方戏的名演员征聘到这里,从而使扬州成了聚精荟粹的地方。《插图本中国戏剧史》中认为扬州“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因而成为南方戏剧活动的集散地”[3]。上述史论从各个层面分析扬州成为戏剧中心的原因,各擅胜场,但是深究起来,应还有一些原因是上述著作没有注意到的。
扬州地理位置处于南北交通要塞,从客观上为南下北上的戏剧群体提供了驻足竞胜的城市外部空间;因盐业和漕运造就扬州的经济极度繁荣,为戏剧的演出提供了经济基础;经济繁荣下发展起来的市民阶层又有着迥异于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这也为各种戏剧的存在提供了潜在的观众群体。但是扬州这一空间到乾隆年间成为了花雅之争的重心,其原因远远不只这些方面。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说过:“城市是解放的前沿,是通向希望和可能性的转折点……城市是产生个人意识、闪现各种印象的环境。”[4]以往学者更多关注了扬州作为戏剧中心的外在物质条件,但作为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初期特征的城市,扬州所具备的人文环境、社会哲学思潮,为扬州成为戏剧中心提供了内在的支撑和动力。
扬州成为戏剧中心的原因,杨飞在其博士论文《乾嘉时期扬州剧坛研究》中说道:“与扬州浓厚的地域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这既包括以盐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文化,也包括竹西歌吹之盛的剧艺传统以及文人荟萃的人文传统。”[5]明清易代之际,扬州城市经历了巨大的创伤,社会结构、城市布局、人口规模等都发生了变化。有人甚至认为“1645年是扬州城市发展的一个分水岭”[6]。在易代之际,“扬州十日”这一历史事件彻底摧毁了传统的扬州,城市的社会文化有没有改变呢?新闻家范长江(1909—1970年)写过一首诗——“扬州有两个,一堕一英豪。炀帝花柳客,盐商亦其曹。史公正气雄,八怪品亦高。而今劲更足,鲜花朵朵飘。”[7]可见在这场屠城惨案发生之后,扬州城市的气质、传统也在发生着悄悄的改变。另外,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扬州城市的规模也迅速扩张着自己的体量,并由传统的城市到新兴城市进行着转变。人口的迁移,城市社会阶层的变化,文化哲学理念的转变,都为扬州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也为花部中心城市的确立扫清了障碍。
一、城市移民与文化融合对花部的接纳
城市的文化传统和气质的变化,是由居住在城市的人群决定的。特别是经历大的人口动荡和移民的城市,更容易发生此种变迁。扬州作为一座性质复杂的要塞城市,“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扬州在发生政治冲突的时候成为军事堡垒,在统一的时候又转变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18世纪,扬州的人口可能已经大量地增加,而且包括大量的外来移民,明代晚期,非土著人口在数量上十有八九超过了土著人口。”[8]
清代初期,经历过扬州十日的惨案,扬州城市人口锐减。按照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中记载,从1645年4月25日到5月2日,“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 其落井投河, 闭户自焚, 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9]。经历兵燹之祸的扬州,“民膏锋刃几尽”,城市居民或逃或亡,十室九空,几不成市。按照傅崇兰在《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中的数字,康熙十四年(1675),扬州城仅有24800人(此数字遭王振忠质疑,认为扬州城市此时人口应比这个数字要多)。但是到了乾嘉鼎盛时期,扬州人口规模达到40~50万人[10]。这些人口中除却极少数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之外,有相当大数量的人口是由外地迁入扬州的移民。
孔尚任在《与李畹佩》一信中指出:“广陵为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广陵,盖如百工之居肆焉。”[11]乾嘉年间,扬州城中“商民杂处,多达数十万家”。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十二《杂记下》记载道:“(明代中后期)山陕之商糜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两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父子兄弟分属两地。如莱阳之戴,科名仕宦,已阅四世,族尽在扬。此外,如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12]由上述资料可见,清代扬州城内的移民来自全国各地,移民身份也是各种各样如商人、为官之人、文人、一技之长者等。这些扬州城市人口多由外来迁入者填充,这一社会人口构成造就了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城市文化氛围。
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使得原有城市空间显得越发地狭小,“闤阓密联,檐牙参错,居者鳞次猬集,行者毂击肩摩”[13]。特别是外来富商定居扬州,在河下一带形成华屋连苑的富商聚居区,“郁郁几千户,不许贫士邻”。形成了特定的新贵阶层,社会阶层的变化也影响着城市的居住格局,改变着城市的审美趣味。1732年,因为扬州城市人口骤增,分两县共治扬州城。旧城西半壁,新城南半壁,为江都县治;旧城东半壁,新城北半壁,为甘泉县治[14]。扬州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而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大,规模的扩大又造就更多的移民涌入。操着南腔北调的外来人口无形之中改变了扬州文化的基因组合。美国建筑学家路易斯·芒福德指出:“城市是一个集合体,涵盖了地理学意义上的神经丛、经济组织、制度进程、社会活动的剧场以及艺术象征的各项功能。城市不仅培育出艺术,其本身也是艺术;不仅创造了剧院,它自己就是剧院。正是在城市中,人们表演各种活动并获得关注,人、事、团体通过不断的斗争与合作,达到更高的契合点。”[15]
扬州经历明代与清代的移民风潮之后,其实已很难再保持其原有的独特地域文化传统,反而是由各地移民带来的新的文化风尚,结合本地文化逐渐形成具有吸纳性、包容性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使得这座城市善于吐故纳新,独领风尚。甚至有学者直接把盐商江春组建花部戏班之举视为“扬州作为熔炉的证据”[16]。经历了清初战火以后,扬州城的传统又一次被破坏,经由大量移民带来的各种文化的交锋,城市再次孕育着新的审美风尚并逐渐展现在戏剧剧坛之上。
二、社会思潮的解放为花部戏剧的兴盛扫清了障碍
由清代明的朝代更迭以后,清政府开始一系列的治理措施。经济上采取重农措施,强调以农为本,并逐渐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思想上采取高压措施,大兴文字狱,以程朱理学为尊,大肆宣传“存天理、灭人欲”等伦理谬论,全面推行道德礼教的下移运动。
此时期的文化思潮承接明代嘉靖以来的启蒙思想,以“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执着精神继续深沉反思,推陈出新且各有侧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概括清代思潮:“简而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17]此时期有以黄宗羲、唐甄为代表的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以顾炎武等人以实用为出发点的“实学”思想;以方以志、梅文鼎为代表的“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思想。由清初到乾嘉时期,社会启蒙思潮达到全盛,诞生了分别以戴震、惠栋为首的皖派、吴派,以及融二者之长的扬州学派。
张舜徽先生在论及清代学术思想之时认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精专,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18]以王念孙、汪中、焦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海纳百川之胸襟,汲取南北各派思想的精华,形成的融通之学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并影响着扬州城的思想,并最终引领扬州艺术甲于他郡的呢?
有学者认为“早期启蒙学术中包含着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前进运动的三大主题:个性解放的新道德、科学与民主”[19]。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扬州学派各位先哲以各种形式反驳着统治阶层提倡的主流论调,并体现在自身的学术实践当中。
乾嘉时期,戴震对于封建统治者吹捧的节烈观、忠孝观等异化伦理体系,企图通过“以理杀人”的本质进行驳斥,从自然人性和理欲关系进行彻底的反叛和颠覆。认为“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欲、情、知的“血气心知”乃是自然人性,只有“遂己之欲,广能遂人之欲”。焦循作为私淑戴震的未及门弟子,对戴震之学服膺有加,并结合自身的见解发扬着义理思想。他在《读书三十二赞》中曾经赞誉戴震:“性道之谭,如风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诸掌。”对于统治阶层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令来推行“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思想,焦循激切地认为:“不知格物之学,不能相推。而徒曰遏其欲,且以教人曰遏其欲,天下之欲可遏乎哉!”作为扬州学派的另一位著名人物,阮元也积极地赞誉人欲乃是天性,认为:“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
个性解放方面,乾嘉时期的学人表现出向晚明复归的倾向。戴震提出:“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20]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来揭露吃人的旧礼教,批判统治者的“舍情求理”。郑燮则直呼:“青春在眼童心热,直摅血性为文章。”谴责礼教束缚,呼吁自由天性。
鉴于乾嘉时期的文字狱,扬州学派的学者们对于统治者采取的“钳口之术”,借研究训诂文字、名物制度等考据之学,达到“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进而借圣人之口来为自己立言,已实现对专制的反抗。在那个道路以目的时期,虽不敢直言,但“其蓄必深,其发也必烈”。
扬州城市经历了清代前中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在戏剧艺术领域则表现出了空前的解放。这种解放,以人性、人欲的天然释放为起点,消解着官方在艺术领域的思想禁锢。嘉庆三年,花部戏曲的兴盛引起清廷的关注,并为此下令禁止:“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蝶亵,即怪诞悖乱,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21]在官方看来,此等靡靡之音乃是引诱人欲、破坏伦理的毒草妖花,会导致“流风日下”。可这些新兴剧中却恰恰代表了世人对于雅部昆腔的厌恶,进而对于所谓正统伦理道德的反叛,是风俗人心的自然情欲的释放。据当时人记载,雅部昆曲被人戏称为“困曲”,闻听演唱昆曲,辄哄然散去。当听到是乱弹之时,则“赚得燕人笑语颠”,甚至把乱弹演员称之为“戏妖”“坑死人”,但众多观众仍对其九死不悔,狂热追捧。只因为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最本真的欲望。这样受人欢迎的花部乱弹,在统治者那里却被视为“狭邪蝶亵”“怪诞悖乱”而加以禁止,但是人最本真的情欲如何禁止得了。
商业的繁荣、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滋长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学术思潮反过来又对于社会行为模式产生着极大的影响。以扬州学派为代表的学术思潮及时回应着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且以融通、客观、科学的进步思想推动着扬州城市作为江南戏剧中心的发展。整个城市发生着思想、行为、审美等方面的转型和变迁,为扬州的发展提供了活力,也为戏剧中心城市的确立和花雅之争的到来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三、商业发展影响着扬州雅俗文化的消长
乾隆年间,诗人沈业富有《题画舫录》一诗:“广陵从古繁华地,遗迹欧苏幸此留。一自六飞巡幸后,湖光山色冠南州。”[22]袁枚也曾赞乾隆年间的扬州“为风尚华离之所”。当然这得益于扬州以盐商为主的经济支柱。据清代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记载:“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商,故谚曰:一品官,二品商。商者谓盐商也,谓利可坐获,无不致富,非若他途交易,有盈有缩也。”[23]盐业的繁荣又带动了其他手工业、服务业、出版业等经济形式的迅猛发展。背后则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围绕着市民阶层所兴起的雅俗文化审美变化。
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清代中叶,士人普遍改变了原来对商贾的鄙薄之见,认为“货殖者,天人古今之大会也”。甚至认为“为士者转益纤吝,为商者转敦古谊”[24]。士作为“四民”之首的认识已经被颠覆,商人的形象与地位则迅速得以提高。按照郑板桥的说法:“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25]这种便民的特征使得商人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超越了传统士人,士人反而是“于民大不便”了。这种不便,或许是由于“儒者知义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26]。因为士人“舍利不言”的传统陋见,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所以“社会的发展已不允许庞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坐而空谈道统了,从中分化出一批人下海经商其实更有利于社会进步”[27]。
伴随着江南地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日益瓦解,而矿业、纺织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以盐商、官商、士商、手工业等小商贩组成的复杂身份背景、文化层次的市民阶层开始崛起。相对而言,传统文人社会地位有所下降。随着以商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其审美习惯也逐渐成为一股潮流。加之此时期的商人文化程度不高,其审美与普通大众相近,反而形成了社会多数派,这又反过来影响着地位下降的士人的审美趣味,最终造成了此时期以普罗大众审美趣味为主体的潮流。
在绘画领域,扬州八怪可以说是社会审美变迁的一个缩影。当时绘画界对于雅俗的界定与戏曲相类。文人则雅,画工则俗;文人趣味自是阳春白雪,民众审美则是俗不可耐。可在当时“八怪”作为一个既是文人、又是以卖画为生的士商群体,自然得以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审美为标尺。这一复杂的身份,使他们缩短了与职业画工的距离,也缩短了与普通消费者的距离,更有助于打破雅俗界限。所以他们在作品之中,以普通消费者所能接受的趣味为创作原则,力主平民化和现实性,善于表现个体与社会的冲突,歌颂普通事物的重要价值与顽强生命。这种新的绘画风格,以个性鲜明的感情与识见接近了市民的审美需求,赢得了消费者的浓厚兴趣,也获得了最广大的市场。
在戏曲领域,更是体现着这种雅俗文化的消弭和竞争。自乾隆南巡以来,两淮盐政“例蓄花雅两部”来看,花部已经在扬州城内有着重要一席。而被视为“土人”的扬州本地乱弹戏,和其他同为乱弹的梆子腔、罗罗腔、高腔等声腔剧种在昆曲歇息之时也能进城“赶火”演出,可见其市场份额及受众也是不小的。甚至连居住在乡下的焦循都认为:“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28]认为雅部昆曲因为在音乐和剧本上的“繁缛”,不符合新兴观众的审美。而“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也更加符合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的娱乐需求。另外,传统雅部多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事,与普通观众生活相去甚远,自然得不到普罗大众的青睐。
按照经济学规律来看,有需求就有商品生产。因此,社会主体审美接受的转变自然也就反映在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之上。乾隆年间,王崧看到云南采矿业快速发展时,周边一些产业也迅速被带动起来。“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而优伶戏剧,奇邪淫巧,莫不闻风景附,觊觎沾溉。”[29]在扬州这样繁华的城市,景象也是自然如此,以至于城市中为这些有需求之人建造了固定的娱乐场所。据《邗江三百咏》中记载,扬州于嘉庆年间分别建“固乐园”“丰乐园”等戏馆。“踵事增华,聊以待腰缠之集。”[30]这些戏馆,即为商人宴集、洽谈提供便利,又能因此谋利。
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雅俗界限被逐渐打破。为了迎合更广大的消费市场,城市中的艺术无不随着消费者及时进行着自身的调整。在雅俗的争斗中,代表少数士人阶层审美的阳春白雪最终被广大市民阶层的通俗审美趣味所打败,也直接成就了扬州花部中心城市的地位。
小结
首先,乾嘉时期的扬州作为一个南船北马的必经之地,交通四达、商业繁荣,自然得风气之先。在戏剧中心城市由苏州向扬州北移的过程中,显然不仅仅是上述原因所能概括的。随着清初移民的到来,改变了扬州传统社会格局。“‘新来的富人’实际取代了‘传统’精英的支配地位……扬州的社会经济权利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来群体的手中,他们控制着城市腹地的主要贸易资源。”[31]移民不仅带来扬州城市的经济复苏,随之输入的外来文化与扬州本土文化相融合,也在悄悄改变着扬州原有的文化传统,更影响着扬州剧坛即将到来的花雅之争的格局。
其次,社会思潮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变化。从反对空谈理性到经世致用发展到乾嘉时期蔚为大观的扬州学派,他们以启蒙者的姿态,回应着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复兴潮流。他们对清政府提倡的主流伦理道德进行着批判和反抗,解放着这座城市的思想;用书写春秋的笔法让圣人替自己立言,为“血气为之动荡”的花部戏曲的流行扫清了道路。这些学者用以变化、发展的观点分析事物,用求同存异的学术态度扩大了研究考证的领域和范围,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不但把“瓜棚柳下”的戏剧艺术纳入他们关注研究的对象,甚至敏感地预测到即将到来的一场剧坛革命。
最后,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他们的审美对于扬州花部城市中心的确立起着最直接的影响和改变。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雅俗界限被逐渐打破,花部戏剧成为扬州城市主要的艺术种类。
总之,占据中心地位的扬州,以新兴城市的姿态,欣然接纳新兴艺术的花部。这也是后来花雅之争中,花部最终能够在扬州蔚为大观的重要原因。
注释:
[1]张福海:《中国戏剧的第五次审美变迁》,《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1期
[2]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下),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727页
[3]叶长海,张福海:《插图本中国戏剧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366页
作者贾战伟
《乾嘉扬州戏剧中心城市确立原因探析》
- 花卉园艺论文盆栽花卉养
- 科技改革论文简析邓小平
- 新闻论文发表媒介终端化
- 内蒙煤炭论文发表分析煤
- 电气自动化技术新发展运
- 中国外语教学期刊征稿目
- 液压与气动杂志2016年目录
- 中级科技职称论文范文:
最新优质论文
- 评价期刊质量的指标
- 两三千字论文能发核心吗
- 写车床维修论文参考哪些
- 中国民族博览是艺术类核
- 最新!锡林郭勒盟在全区
- 如何让sci杂志延长修稿时
- 施工技术期刊发论文要求
- cpci是什么领域论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