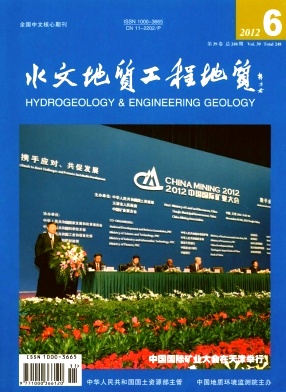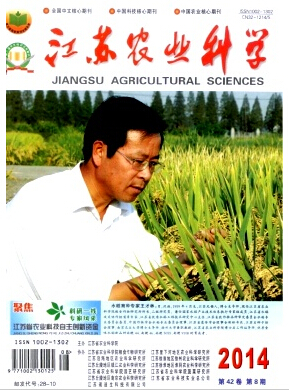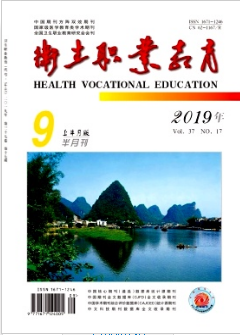戏剧史上“婚变”剧的流变与审美范式的实现——以南戏《琵琶记》为例

摘 要:作为南戏代表剧目,婚变戏剧《琵琶记》改编自早期南戏《赵贞女》。该作品经过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双重选择之后,其审美范式实现了由《赵贞女》中超自然情节的恶有恶报到《琵琶记》中的善有善报。情节和结尾的转变,既有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受众的选择。这种圆满结局,对后世戏剧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关键词:《琵琶记》;婚变戏剧;审美范式

一、从《赵贞女》到《琵琶记》
在高明创作《琵琶记》之前,赵贞女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南宋陆游有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 与陆游同时期的另一位诗人刘克庄也在《后村诗话》中提到蔡中郎的故事:“黄童白叟往来忙,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1]可见在《琵琶记》创作之前,赵贞女与蔡二郎的故事已经被说唱艺人搬上了舞台,并在农村各地广为流传。此时,蔡中郎的故事被附会到东汉文人蔡邕身上,成为宋元民间说唱文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蔡邕,字伯喈,东汉陈留人。据《后汉书》记载,蔡邕天性笃孝:“母常滞病在床,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着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理——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2]在这些诗词中并未提及民间故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样子,但是从陆游等人的诗中可以看出,民间说唱艺术中的蔡中郎形象一定与历史相去甚远,所以陆游在诗中才会表达自己对于这种附会和虚构的不满。
被称为“词曲之祖”的《琵琶记》则脱胎于早期南戏作品《赵贞女蔡二郎》。该作品作于南宋光宗朝年间,作者不详。据徐渭《南词叙录》记载:“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3]明祝允明也在《猥谈》中谈到:“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真女蔡二郎》等。”[4]早期南戏《赵贞女》大致的故事情节是:蔡二郎与赵贞女婚后不久即进京赶考,贞女在家侍奉公婆。由于蔡二郎久无音讯,加之岁值荒灾,贞女进京寻夫。此时蔡早已京师为官,不但不认赵贞女,且打马踩死赵贞女。后蔡伯喈因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
元末,高明将民间流传的《赵贞女》结合历史改编成了《琵琶记》。当然意图也相对明显,开场《水调歌头》曲清楚地道出了个中缘由:“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也有人说开场词为明人伪作)本为谴责书生负心的主题变成了戏曲中宣扬的忠孝节义,为这一婚变题材的作品增加了新的故事内涵。明传奇以《琵琶记》这种大团圆的结构为圭臬,进行了大量此类旧作的改编与重写,一时蔚为大观。
二、以《赵贞女》为首的婚变题材戏剧作品与审美范式的初现
明代沈璟曾将南戏中的婚变戏剧写成了《书生负心》的散套,其中《刷子序》曲云:“书生负心,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张叶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无情李勉将韩妻鞭死;王魁负倡女亡身。叹古今,欢喜冤家继着莺燕争春。”[5]这里包括五个南戏剧目《陈叔文三负心》《张协状元》《李勉负心》《王魁负桂英》《欢喜冤家》。另外写婚变戏的还有《张琼莲》《崔君瑞江天暮雪》等。可见,在明代,戏曲创作者已经深深认识到婚变题材戏曲的繁多以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
所谓的婚变戏,是在早期南戏中较多出现的一个戏剧母题。大致内容均为青年男女在贫困之时结为夫妇,后男子赶赴科举考试,妻子在家等候丈夫归来,等来的却是丈夫高中之后的抛弃。最后戏剧的结局是作为羸弱一方的女子凄惨死去(有时甚至是被变心的丈夫虐杀,如赵贞女、敫桂英等)。在宋代时期,这些负心戏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两宋时期,广开科举,网罗中小地主阶层及下层士子。这些贫寒士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地位的陡变,使他们由白衣之身而步入卿相权贵之间。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命运的飞黄腾达使他们抛弃结发妻子,入赘豪门。而这些妇女由于男子的变心,带给她们的却是致命的打击和摧残。这种情况引起了中下层阶级的警醒和反感,作为草根意识形态直接代言人的艺人们自然而然地要对这种情况予以严厉的批判。在戏中他们借助神灵的力量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抗争,还社会一个公道。
“戏剧本为美术文学的范畴,神鬼迷信之事,以科学之眼光视之,甚为嗤笑,以美术文学之眼光视之,则甚有趣味。夫戏剧本非真事,何妨留此借增兴味耶!”[6]由于,目前我们已不能看到此类南戏的具体形式、故事内容和故事情节,但是我们通过这些戏剧的结局依然能够看到艺术审美范式在婚变题材中的彰显。
一般来说,艺术审美的善恶评判在婚变题材的戏剧作品中是充当着社会道德与审美代偿品的功能的,也是普通民众善恶评判标准的舞台直接体现。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夫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且随时可以休妻再娶。但是“妻子则是不能随便提出离婚的。若真有为人妻子而擅自离去者,按律要‘徒三年’”[7]。这种不公平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助长了男性弃妻再娶的恶习,也增加了社会悲剧的发生几率。特别是这些为人妻者,忍辱负重,耕织贸易,一人承担家中的责任和劳作,以供丈夫科举考试。可是这些寒门学子,一旦科举成功,便纷纷另择高枝,另娶权贵豪门女子为妻。于是,社会上“薄命女子负心汉”的悲剧便大量出现,社会公正无法伸张。在这种弱者受欺辱、正义不可得的背景之下,受众需要一种心理补偿,让这些正义在艺术世界中得到实现和伸张。
这些美好善良的女性在家庭婚变中失去了性命,更是激起人们对于道德审判和社会公平的期待。于是在艺术创作领域内,往往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呈现恶有恶报的艺术审美范式和标准。在戏中他们借助神灵的力量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抗争,还社会一个公道。而这些负心之人无不受到惩罚。例如:蔡伯喈遭暴雷震死,王魁为桂英之鬼魂索命,陈叔文把兰英推入江中,后亦被鬼魂索命。他们往往通过这些超自然的复仇行为来完成艺术正义的呈现、社会正义的替代和弥补。
三、翻案之作《琵琶记》与婚变戏剧艺术审美范式的形成
高明创作《琵琶记》之时,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前面谈到,早期南戏中,男子负心的婚变戏剧较多,但到了元代,这类题材的戏剧数量明显有所下降,其主要是因为元代读书者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甚至有“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特别是元朝统治者甚至在制度上明确进行种族歧视,且取消了科举考试,断绝了汉族士子的仕途之路,读书人不再具备“富贵变心”的社会环境,相反家庭悲欢离合故事却普遍起来。于是,对前代负心故事做翻案处理的南戏作品也就多了起来。高明创作《琵琶记》就体现了南戏戏剧创作的这一历史转变。它既是南戏雅化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最高峰。
徐渭《南词叙录》中曾言道:“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记雪之。”[8]而且高明在《琵琶记》开篇明确指出戏曲作品“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教化使命(有人曾质疑篇首之文为明人伪作,且作一说)。在作这个翻案文章之时,作者是带有与其他作品完全不同的创作责任感去重构故事框架、再塑人物形象的。另外,随着南戏的成熟,戏剧演出渐渐由乡村走向更加广阔的城市。时代审美的变化,受众层面的变迁,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作品的改造和翻新。高明在进行《琵琶记》的创作之时,为了适应社会审美和翻案之需,尽力避免以前戏剧作品结尾的恶有恶报这一道德审判结局,而是力求达到“善有善报”这一美好结局。为了达成这一艺术目的,对旧有的故事情节和戏剧结尾进行了彻底的改写。以“三辞三不从”为主要关目,通过“善与善的冲突”,重塑了蔡伯喈这一符合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
作品也对赵五娘这个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的塑造。作品通过“糟糠自厌”“代尝汤药”“断发葬老”“描容上路”等情节,替我们塑造了一个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更符合男权社会认知的具有所有传统美德的古代女子形象。在赵五娘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国女性的诸多美德,她的苦尽甘来、夫妻团圆在后世得到无数读者的认同。而她的“善有善报”也更加符合受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因此明代王世贞在戏曲论著《曲藻》中曾评价道:“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功、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之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9]
从《琵琶记》的创作意图来看。高明想通过此戏剧达到妻贤子孝、合之双美,最终达到雅俗共赏之目的。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也确实是达到了这一效果。以蔡伯喈为代表的忠孝节义形象受到了当时统治者们的欢迎。朱元璋曾说过:“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而且《琵琶记》的“生旦团圆,举家旌表”的结局套路也获得了明传奇婚恋剧的大量沿袭,一时蔚为大观。但从后世的演出来看,“除去末、净、丑的戏和热闹的群戏外,以赵五娘为主的折子有《关粮》《抢粮》《吃饭》《吃糠》《剪发》《卖发》《描容》《别坟》《弥陀寺》《廊会》等,此外还有与蔡伯喈同场的《称庆》《南浦》《书馆》等折,占了全部折子戏的大半”[10]。从受众的选择来看,作者的主观意图在舞台演出层面上是大打折扣的。在清代中后期,舞台演出更是倾向于对于受苦受难的赵贞女的呈现——“在折子戏形成之后,戏剧舞台演出的‘全本《琵琶记》’一般都只是将有关赵五娘的十来个折子加上一些净丑戏串联而成,除了赵五娘的结局不同,这实在是一部高度雅致化的《赵贞女》。”[11]
《琵琶记》创作初衷是为蔡伯喈这一历史人物翻案,但是在实际的舞台演出过程中,受众更倾向于对于困难承受者的关注和同情,艺术正义的实现更倾向于对于“善有善报”的自然呈现,而没有以创作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
小 结
家庭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样存在着不公与特权的问题,特别是早期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让处在弱势的女性更容易陷入危险的境地。而作为舞台艺术的戏剧,少不了爱恨情仇的抒写与公平公正的呈现。从早期南戏的《张协状元》《赵贞女》到后来《琵琶记》《珍珠记》以及花部戏《秦香莲》等作品,不管创作者借助超自然的神鬼力量实现“恶有恶报”的审美范式,还是主观倾向“善有善报”的圆满结局,婚恋戏剧中的情节和结局里面主观和客观的结果都是属于彼时彼刻的道德胜利。社会秩序的不公与混乱,法律的偏袒和缺席,都通过艺术作品来完成道德与社会的公平。民间创作者和文人作者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质朴世界观来维持精神世界的公平和正义。
注释:
[1]侯百朋编:《琵琶记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 35页
[2]范晔著:《后汉书》(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79~1980页
[3]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21页
[4] 祝允明撰:《猥谈》,《古今说部丛书》(五),清宣统至民国间上海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第4页
[5] 沈自晋编:《南词新证》,《善本戏曲丛刊》(第三辑),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58年,第221~222页
[6] 张福海著:《中国近代戏剧改良运动研究1902—19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2页
[7] 吴宝琪著:《宋代的离婚与妇女再嫁》,《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第77页
作者马方方
《戏剧史上“婚变”剧的流变与审美范式的实现——以南戏《琵琶记》为例》
- 花卉园艺论文盆栽花卉养
- 科技改革论文简析邓小平
- 新闻论文发表媒介终端化
- 内蒙煤炭论文发表分析煤
- 电气自动化技术新发展运
- 中国外语教学期刊征稿目
- 液压与气动杂志2016年目录
- 中级科技职称论文范文:
最新优质论文
- 写车床维修论文参考哪些
- cpci是什么领域论文数据库
- 中国民族博览是艺术类核
- 评价期刊质量的指标
- 最新!锡林郭勒盟在全区
- 如何让sci杂志延长修稿时
- 两三千字论文能发核心吗
- 施工技术期刊发论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