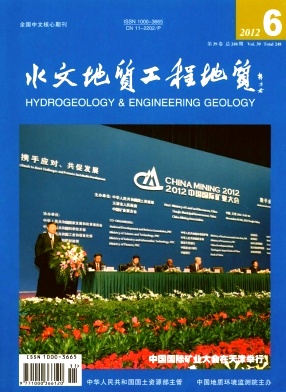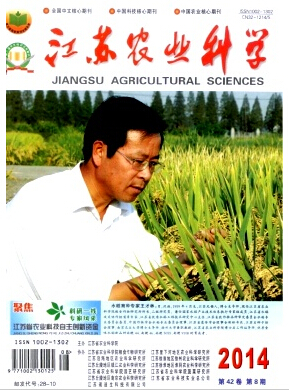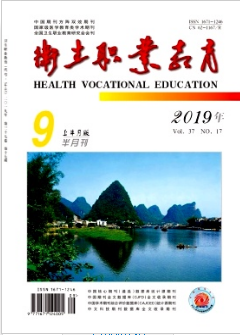解释之道与视域融合——宋人解《庄》的意义

摘 要:本文从后学对《庄子》解释的时代差异出发,跟踪中国古人对思想世界的特殊表达。正是对文本解释差异的尊重,才本质性地完成了文本经典化的塑造过程,而这也是经典文本“撒播”思想的“经过”之路。从宋人释《庄》解《庄》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就是以这种敞开与融合相应的思想的方式,形成了极具东方特色的“解释学”之路:作品经过的路,其实也就成了作品本身。
关键词:《庄子》;解释;差异;视域融合

《庄子》成书传世讫今,后学之评注与解释可谓差异纷呈、繁荣不息。而对经典文本解释差异的尊重,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敞开并显露作为经典的《庄子》所“经过”的道路。德里达在对西方传统文本承续的知性反思中,曾以“延异”(difference)作出解释。“延异”表达出在对文本的理解过程中,是突现差异的,但正是对文本传承中差异的尊重,才转而表达出对文本本身的尊重。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今本(郭注本)仅为三十三篇,已佚十九篇。就算班氏孤说难信,但司马迁言“庄周”著书十余万言,今所见仅六万余言,可见亡佚为实。唐人陆德明《经典序录》中说:
“《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2]
若据此言,可见《庄子》书在晋人处已大获改观。事实上,从晋人辑注《庄子》开始,《庄子》书言已经被打上了时代“烙印”。时言:《庄子》注“郭象”,还是“郭象”注《庄子》?此语恰如《齐物论》处庄周所言:吾今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梦为庄周与?本身已经表明《庄子》书所具有的历史渗透力。同时,也可看出,今天所见《庄子》版本的时代印迹。而这个“印迹”绝非《庄子》所加,实乃后人之所为。晋人尚任“自然”,除郭象辑注本表达出晋人思想意向外,还有向秀、嵇康等对《庄子》思想的注评及诠释。“托物言志”,寄托精神,借此物而言他,这是中国古人对思想世界的特殊表达。这既是文本经典化的塑造过程,也是经典文本“撒播”思想的“经过”之路。中国古人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形成了极具东方特色的“解释学”之路:作品经过的路也就成了作品本身。这种路径不仅表现在《庄子》身上,更表现在《论语》《道德经》等经典作品当中。这个道路不仅表现在古典时代,而且它还将持续下去。这是否也在说明:对文本理解上的差异,恰恰是对文本思想的尊重。
世疑郭象因其意志而辑《庄》删《庄》,看来并非没有道理。郭象之举,功矣?罪矣?此学术公案,实难定论。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从《庄》学诞生到晋人处复活,其学术踪迹,竟有数百年的沉寂。数百年的沉寂中,《庄子》到底显身何处?就此而言,晋人之举,不能不说是“撒播”《庄》学旨要的大功绩。但就《庄》学从沉寂到复活的漫长历程来看,也足见播传思想道路之艰辛。其间既有文士学承之喜好,又有时人随附俗雅之风气;既有他学他说之排异,又有他说他学之容蓄。所谓“特会庄生之旨”,可能既为定评,也为疑肇。希腊智者赫拉克里特言:上山之路,就是下山之路。喻于《庄子》或许就是:其中道绝断处,往往就是其开始走向“踪迹”活现的道路。而惟此思想“撒播”之路才不会绝断。
二自晋人之后,《庄子》研习之风日盛。唐人学风开朗,多类学说并举于世。故《庄》学解注,既为文士所喜,又为世风所取。唐代乃诗歌之盛世,而《庄子》汪洋恣肆,不为拘羁的文气和思想,大投文士喜爱。李白等诗歌大师作品中灼见《庄》学印记。而从成(玄英)疏注本和陆(德明)音义本中,也见这一时代各家并蓄,儒释道交相融合的“解释学”局面。自宋代以来,注《庄》解《庄》进入了一个敞开与融合相因循的大时代。宋代也是文化盛世,尤其政设制举倾向文人,解《庄》注《庄》自然能够很好地承续唐人局面,同时宋人又拔异超高,在新的文化气象间,营造出了儒、释、道合融的思想格局。尤其苏轼首度阙疑诸《庄》篇,开始有意颠覆自司马迁以来的定论。这不仅开创了后世考据《庄》学的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倡了一种通过会通文意,内在把握其精神旨要的读《庄》之风。苏轼《庄子祠堂记》云:
“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意,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味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3]
苏轼的阙疑,既来自于对《庄子》思想内在的会通,也为符合晋人解《庄》注《庄》的方向,后世学者,在对《庄子》诸篇之真伪的辨别上,通过会通精神气象,极为内在地把握《庄》学实际,这其实才是读《庄》,解《庄》的极高明之处。太史公说《庄子》风格乃“洸洋自恣以适己”。太史公之说可谓点到《庄》文实处,这与《庄子》自说极为一致。《天下》篇说“庄周”: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倚见之下。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其书虽环玮,而连忭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者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1]
“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可见古来才性“洸洋”之作,非才性恣肆之人,实难领会其高妙“叔诡”之意。读《庄》解《庄》,其理解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庄》“对话”(“与庄语”)的过程。“敖倪于物”,谴于是非,“以天下为沈浊”之人,不要说在洸洋辟阔之境,心领神会《庄子》了,甚至根本就接近不了《庄子》。而这恰恰也是近代“解释学”所要开辟的路径:通过历史“想象”(对不在场性的调动)绽示作品所处的内在处境,通过“对话”显现作品所承载的内在精神。
苏轼解《庄》,凭才资悟性,直击《庄子》之文,从而高会其意。才性高低,实乃天授。然天授之才,若非“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4],也不可“与庄语”。《庄子》尝言:嗜欲深者天机浅。意谓,人生与世,当“与世俗游”,然而,若不超然放物,忘情自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则纵其才质绰约,悟性极高,也终以“天地为沈浊”,为世法所“胶固”。此可谓,天下学人所共识。宋人中深得“理学”之道的陈颢、陈颐,就曾劝人:
“若谨礼者不透,则是他须看《庄子》。若他极有胶固缠缚,则须求一放旷之说以自适,譬之有人于此,久困缠缚,则须觅一个出身处。”[5]
读《庄子》书,盖能“涤除玄览”,洁清“沈浊”,然,非能“涤除玄览”,洁清“沈浊”者,又无法“观其书”。自古“观其书”者,皆如郭子玄语:
“故观其书,超然自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恍之庭矣。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暂而揽其芳余,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犹足旷然而忘形自得之怀,况探其远情而玩永年者乎?”[4]
苏轼的阙疑,来自其读《庄》时所获的独到领悟。至于其得出是否合于《庄子》原貌,我们姑不追究。但其所得结论,却来自“与庄语”内在而精微的过程,确实是自古以来读《庄》解《庄》的高明手法。但也不得不说,苏轼的疑问,也有其特殊的思想动机。在《庄子祠堂记》中苏轼说道:
“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箠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离、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3]
苏轼以为太史公之语《庄子》以文言诋訾孔子之徒,乃知庄子之粗也。而不知庄子实助孔子。我想东坡此说,盖本乎二因:一本乎《天下》篇未述列孔子之说以作评,“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二本乎道学文言之“正言若反”(“倒行而逆施”)的道理,“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此说是否中肯,尚待商榷。但东坡以庄子之言内归于儒者,此动机却很明显。正是信本儒者之尊,他才于微察细觉中得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等诋訾孔子者诸篇为《庄子》伪作。事实上,儒道合源的说法,由来以久,单从《史记》述传孔子晚年问道于老聃一事,就可看出古人认为儒道同源的历史心理。的确,观庄子书,与观孔子书,庄子之说往往切中儒学要义,而且庄子对孔子之徒的言语行迹对说细致,声色并举,宛然立乎其侧。如《天道》篇说: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徽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譒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原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1]
再如《天运》篇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1]孔子见老聃并“语仁义”,篇后还载述了孔子见老聃后的感受: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见乎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脅。予又何规老聃哉’”[1]
孔子将见老聃的感受,喻为“见乎龙”,其徒子贡因之不信:“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也可得而观乎?”结果被老聃一番教说,弄得“蹵蹵然,立不安”。
《史记》尝言:孔子见老聃,始知神龙见首不见尾。司马迁所述,是得之于《庄子》书之记说,还是源于其他传说,今已无法备察。但就《庄子》借老聃之言评说孔学之意,却中其“鹄的”。这不能不说是《庄子》之高明。近人杨伯俊在释解孔学著作《论语》时曾说,庄子最懂得孔子,此言确也不虚。他说:
“我认为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6]
以“庄”解“孔”?这是否能够引起近人之注视?这可能还是个问题。但就《天运》篇中载述孔子向老聃诉说治“六经”之难的故事,可见《庄子》所语于孔子甚近: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1]
《庄子》载孔子言行诸多,情境场面也合《论语》之记述,但又多与《论语》中孔子之言说要义迥然不同。无论其“正说”是尊孔之举,还是因其“反说”而判断《庄子》在诋訾孔子之徒,这至少说明庄子是“知道”孔子的行事和主张的。事实上,先秦诸说中诋儒之论者大有人在。墨子及其后学,以及韩非对儒家之徒的诋訾,确不在少数。所谓庄周之学源乎孔门之说,盖《庄子》书言,多“正说”颜回。且颜回在孔子书及庄子书中皆有“道行”,《论语》说其“贫居陋巷,一饮瓢,一箪食,曲而眈,乐在其中”。《庄子》书又多记颜回“坐忘”的过程和修迹。此“孔颜乐处”,既为先儒修身境界,也合道家无为之趣。让人因此想到颜回之学及于《庄子》,也是情有可原的。但若因此就说庄周之学本源乎孔子,则未必有实据。若依此说断定庄周学渊出自孔儒,那么庄周之书也多有诋訾名辩之辞,是否也因此认为庄周之学本乎名辩之徒呢?
《庄子》书多言孔子之事,或诋或誉,不一而足。但其书写言情并茂,声色并举,的确见其书写艺术之高明。世人常以孔儒正统学说为孔子申名立说,但如道家书等所载孔子之言行,往往视为讹化,这实不是得品古人思想全貌的途际。除《论语》里的孔子外,《庄子》里面的孔子,是否也算是一种对孔子全说的窥探呢?
《解释之道与视域融合——宋人解《庄》的意义》来源:《甘肃农业》2018年12期,作者:郭吉军。
《解释之道与视域融合——宋人解《庄》的意义》
- 职称论文刊发主体资格的
- 政法论文浅析工会法主体
- 化学在初中教学中的情感
- 中学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方
- 法治论文投稿法治型市场
- 杂志社论文发表浅析推动
- 新疆教育报投稿浅析学生
- 分男女招生录取的合宪性
最新优质论文
- 毕业论文的评分标准
- 晋升职称业绩是什么概念
- 东南国防医药是评职称认
- 公路行业副高评审怎么发
- 职称评审全国通用吗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论文要
- 河北职业教育期刊投稿能
- 工商管理毕业论文选题原
论文发表问题热点
- 发表本科毕业论文准备技
- 抗震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什
- 机器学习算法论文适合投
- 中级职称学术期刊论文发
- 期刊发表论文格式和论文
- 来重庆环境科学杂志上投
- 《科技资讯》省级科技期
- 评职称的论文什么时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