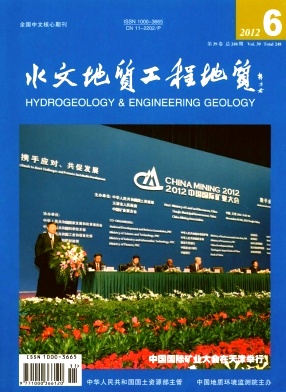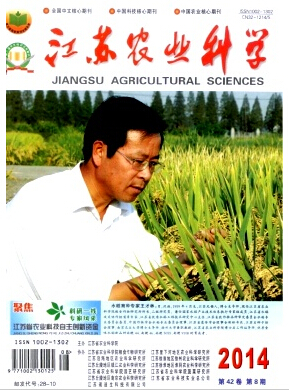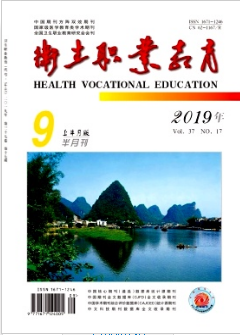陇东南民间美术的历史文化意蕴

摘要:陇东南是连通西北、西南和中原地区的枢纽地带,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造就了陇东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原始文化、周秦文化、氐羌文化、巴蜀文化、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熔于一炉,从而形成了陇东南民间美术历史渊源深厚、艺术类型多样、文化意蕴丰富、区域特色鲜明的特点。这些民间美术以其特有的方式,讲述着陇东南地区复杂深厚的民族历史,彰显着陇东南地区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
关键词:陇东南;民间美术;历史文化;意蕴

一、史前文化的延续——以“抓髻娃娃”为代表的原始崇拜美术文化
民间美术传承了原始艺术精神,与生活融为一体。陇东南史前文化遗迹遍布,丰富的史籍、考古资料与当地民间传说中人文始祖的活动轨迹相互印证,古史传说中的伏羲、女娲、炎黄部落,早期都活动于渭水、西汉水上游地区。原始文化的精神在这里延续,且在部分民间美术造型中打上深深的烙印。
陇东南民间美术的历史文化意蕴/余永红
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总第177期
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龙的传人,最初源头应为伏羲氏族的龙图腾。在渭水、西汉水上游一带出土的石岭下类型彩陶中,流行一种独特的鲵鱼纹,这种奇异动物纹的头部似人面,身子似鲵,张牙舞爪,富有生命活力和神秘的精神意味,与伏羲氏族的龙图腾密切相关,也就是人首龙身伏羲形象的渊源。[4]陇东南一带的民间艺术中就普遍流行龙图像,最典型者是春节期间民间社火中的“龙灯”,其精神内核源于史前的龙图腾崇拜。[5]伏羲“人首龙身”或“人首蛇身”造型其实就是一种将龙人格神化的图腾符号,体现了原始图腾文化的思维方式。在陇东地区的香包造型中,也有一些造型神秘怪异的“人面鱼龙”“鱼娃”“猪头龙”“蛇身娃娃”(图1)等造型,这些神秘奇异的民间美术造型,其文化精神亦源于原始崇拜,是史前图腾文化的延续。此外,陇东南民间剪纸、雕刻、面塑等其他民间美术中的一些祥瑞动物,身躯为动物,头部及五官却是富有表情的人面造型,既体现了民间美术淳朴稚拙的艺术情趣,也传承了史前时期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
陇东剪纸中有一种独特的人物造型“抓髻娃娃”,皆呈对称的正面姿态,双臂上举或下垂,两腿外撇,形象多为女性。目前主要用于招魂、辟邪、燎疳、送病、驱鬼、镇宅、祈雨、纳财、求福等。这种简单而稚朴的造型,却蕴含深厚的原始崇拜含义。此娃娃应与陇东南一带史前时期的人文始祖女娲有关,其功能虽已泛化和世俗化,但其本源文化则源于最初的生殖崇拜。女娲抟土造人故事的实质其实是女娲化生人类,这也符合母系氏族社会结构特征。女娲之“娲”与“蛙”古文字相通,也是后来“娃”字的来源,史前人类对蛙的崇拜,也正是源于蛙类强大的繁殖能力。《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所谓“女娲之肠”,其图像本质与蛙类产卵图像是相同的,真实含义是象征女娲孕育和化生人类。[6]
陇东南一带的彩陶文饰中,也普遍流行蛙纹,到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期,已逐渐演变为当时西北地区许多原始部落普遍崇拜的“蛙神”形象。[7]此蛙神亦与当地的女娲信仰文化相关,蛙神也就是女娲。[8]女娲化生神话在民间影响巨大,所以在历代民间艺术中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这种题材和内涵。陇东地区的抓髻娃娃虽然已普遍用于民间各种宗教巫傩活动中,但其本质和源头仍是女娲神话。抓髻娃娃最初应是象征家族人丁兴旺,这也可以从抓髻娃娃的造型和文饰中得到印证:多数抓髻娃娃都有图案化的生殖器,有些抓髻娃娃还在生殖器的下方,安排一个更小的娃娃造型,其表达的含义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生殖崇拜(图2)。无独有偶,马家窑文化彩陶文饰中亦有描绘女性生殖器的蛙纹,与抓髻娃娃造型极其类似。所以,这种完全对称状的娃娃造型,与彩陶文饰中的蛙纹一样,应是史前生殖崇拜文化的延续,也是原始崇拜文化的活化石。
二、周文化的承传——以春官《春牛图》为代表的牛耕美术文化
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起源很早,渭水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平坦的河谷以及陇东高原一望无际的黄土大塬,也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史籍记载来看,对农业最重视、也最有成就者当属周人。其始祖后稷就是一位农业天才,另一先祖叔均则发明了牛耕,周族也以农业起家。夏商更替之际周先祖不窋率族人逃于北豳,即今陇东庆阳一带,发扬族群传统,利用这里优越的农业资源使部族发展壮大。先周发达的农业开启了我国传统农业之先河,西周政权建立后,通过国家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农业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奠定了我国古代传统农业的基础。[9]居于渭水和西汉水上游的秦人,作为周的诸侯国,在文化上也积极向周人学习,重视农业生产。悠久发达的农耕文明,造就了陇东南一带古朴深厚而多彩多姿的民俗文化,民间美术最具有代表性。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考察,我国传统民间美术其实都属于农耕文化范畴,但部分民间美术类型则直接表现农耕题材。“牛耕”的发明又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所以,由“耕牛”和“农人”组成的《牛耕图》就成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标志性符号。陇东南民间美术中的牛耕题材,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带深厚悠久的农耕文明。
陇东南流行的民间风俗“春官说春”就是农耕文化的缩影。陇东春官为社火队“主角”,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手拿彩扇,以即兴作诗、说吉利话为主,是新春的“传话筒”。陇南春官身穿礼服,肩挂褡裢,一手拿拐杖,一手拿木雕“春牛”,怀揣《春牛图》走家串户说春——演唱古朴的“春曲”,发送图文并茂的《春牛图》。“春官”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是西周设置的六官之“礼官”,其中的“冯相氏”和“保章氏”负责天文历法,观象授时,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10](P71)陇东南民间春官虽然与《周礼》中的春官有根本区别,但也有着内在联系,民间春官是由古代官方春官逐渐演变而来,[11](P758)他们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陇东南民间春官则充当春天的使者,通过说唱、送《春牛图》的形式向农民们报告来年的节气及天文气象,提醒农民按时耕种,不误农时。
《春牛图》为春官自制版画(图3),内容以二十四节气为主,并附有来年的雨水气象信息,是督促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指南。《春牛图》上部为文字,下部绘制一耕牛和农人,图像简洁质朴,具有鲜活的生命气息,洋溢着浓郁的农耕文化意味。既是一件重要的生活实用品,也是一幅韵味十足的民间绘画。自牛耕技术发明以来,“耕牛”和“农人”就成为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图像符号,所以《春牛图》也是农耕文化的标志和索引。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典型符号其实形成很早:《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人方耕,名曰叔均。”[12](P336)古本《山海经》的《海经》和《荒经》部分是以图像为主的,周人始祖后稷之孙叔均是牛耕的发明者,这里描绘的情节正是一幅《牛耕图》;西周以后,官方一直流行“鞭春”习俗,俗称“打春”,就是鞭打土春牛的仪式,由此形成了制作土春牛和耕人的风俗;汉代画像石中已有大量完整的《牛耕图》;宋代开始流行送小春牛、粘春贴等习俗。春官手中所拿木刻小春牛,即源于宋代以来流行的“送小春牛”习俗。版画形式的《春牛图》也至迟在宋代出现,明清至民国时期仍流行不衰。耕牛和农人这种单纯的形象组合,伴随着周人牛耕技术的发明和农耕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并不断凝练,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典型符号。
陇东南民间社火中还流行“娱牛”习俗(图4),当地老百姓俗称“务牛”。就是用纸扎造型方法制作一个耕牛,牛头用竹篾和彩纸裱糊制作,牛身用麻布缝制,表演时前面一人顶牛头,后面一人顶牛身,造型憨厚质朴。“娱牛”表演是一套完整的春耕活动过程,内容从探查地情、散粪、撒种子、耕作、休息、送饭直到结束,耕作时一人在前牵引耕牛,一人在后扶犁,旁边几个老农辅助,唱着悠扬婉转的《务牛曲》,围绕圆形表演场地进行牛耕表演。娱牛是社火队的压轴节目,一般在最后表演,可见其意义之重大。陇东南社火中的春牛和娱牛,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深厚农耕文化结晶。此外,老百姓除了以这种独特的民俗民艺传承牛耕文化,同时在民间刺绣、剪纸、泥塑、面塑中亦塑造憨态可掬的春牛或牛耕图像,这些形态各异、造型稚朴、生动有趣的《春牛图》或《牛耕图》,不仅展现了陇东南民间艺术的灿烂丰富,更体现出陇东南一带民俗的古朴和农耕文明的深厚悠久。
三、秦文化的遗风——以“乞巧”和“香包”为代表的女红美术文化
乞巧在古代是一种各地民间普遍流行的民俗文化,但从相关史籍记载来看,源于秦文化。从历史文献结合陇东南一带乞巧风俗考察,巧娘娘就是织女。赵逵夫先生认为织女的原型是秦人始祖女修,牵牛原型是周人始祖叔均;女修擅织而称“织女”,叔均擅耕且发明牛耕而称“牵牛”。牵牛星和织女星最初是秦人以本氏族杰出人物命名的星名,而后演变为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农耕文化中的牵牛和织女,“天汉”之名亦因汉水(西汉水)而得。[13]可见牵牛织女传说及乞巧习俗早在秦人居西汉水上游时期就已形成了。《水经注·渭水》记载:“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宫,故《三辅黄图》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14](P433)可见秦人进入关中后依然保留和传承了族群的古老风俗。另外,敦煌文书中也有关于乞巧风俗的记载,[15]进一步证明乞巧风俗源于秦人。
乞巧目前主要流传于陇南西汉水上游一带,但从相关调查资料来看,陇东也曾盛行乞巧风俗,而且乞巧的方式与西汉水上游地区基本相同。[16]陇东虽为先周文化发源地,但从文化源流来讲,陇东乞巧风俗亦应为秦文化遗风。陇东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义渠戎居地,秦灭义渠戎后,义渠戎遂为秦民,民族融合必然形成文化融合;另外乞巧风俗在秦汉以后已广为流传,明清以来已成为官方和民间都普遍流行的重要民俗。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乞巧的主题由早期的始祖崇拜逐渐转向祈求心灵手巧,乞巧崇拜的对象由早期的牵牛织女向单纯的织女崇拜转变,乞巧的主体由早期的男女共同参与逐渐向纯女性化演变。巧娘娘(织女)也因为擅织而成为妇女崇拜的智慧女神。妇女乞巧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使自己心灵手巧,并通过精美的刺绣、编织、剪纸、茶饭等民间美术得以体现。乞巧是一种民俗事象,但乞巧的文化基础却是女红文化,乞巧的结果最终要通过女红美术的形式呈现出来。
陇东南一带民间女红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妇女们也通过各种丰富的民间美术造型展示着她们智慧与灵巧。陇东南民间刺绣类型丰富多样,服饰中的肚兜、裹肚、缠腰、出脱帽、虎头鞋、布袜、绣花鞋、鞋垫,生活用品中的枕头顶、老虎枕、门帘、枕套、桌裙等,绣花精美,款式独特而富有乡土气息。作为装饰品的荷包,是陇东南一带端午节期间给小孩和小家畜佩戴的独特刺绣,尤以庆阳香包最具代表性,题材多样,做工精致,形式美好,寓意深厚,不仅装点服饰、美化居室,也充分展示着陇东南妇女的灵巧与智慧(图5)。
除此以外,妇女的勤劳与灵巧也展示在其他一些民间美术造型中。根据节日、红白喜事等需要,民间妇女将食物做成各种造型,例如陇南乞巧中的巧果、端午节的花馍馍,陇东祭祖敬神的花树、婚嫁风俗中的绿狮子、红老虎等,[17](P249-250)不仅增强了食物的审美功能,也表达着美好祥和的精神含义。心灵手巧的妇女们也将各种祥瑞动物、十二生肖、植物花卉和人物等剪贴在窗户上,图5陇东南刺绣《鱼钻莲》
这些剪纸作品造型质朴、色彩绚丽,在阳光的映照下十分夺目。陇东南妇女们这种源于乞巧文化的系列民间美术作品,不仅将生活艺术化,也将艺术生活化;不仅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和谐观念,也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精神。
四、氐羌文化的余韵——以“池哥昼”“羊皮鼓舞”为代表的巫傩美术文化
陇东南自古为氐羌聚居繁衍之地,其文化本身就有氐羌因素,氐羌遗风至今仍蕴含在陇东南民间艺术中。陇东南一带的史前文化就是西北先民创造的地域文化,其主人就是以氐羌为主的西戎部族。仰韶文化以后,向西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向东发展为常山下层文化,至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时期,氐羌部族的文化已覆盖整个陇东南区域。周人和秦人在陇东南期间,一直和戎狄毗邻共处,秦汉以后,陇东南一带仍为氐羌聚居繁衍之地。唐以后陇东南一带的氐羌虽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随着部族的迁徙融合,氐羌文化已融于当地民俗文化中。极少部分人群则在陕甘川毗邻地区的深山险恶地带生存下来,并传承了本部族的古老文化。陇南一带的白马藏族和藏族,就是古代氐羌的遗裔,从白马藏族的居地和族称来看,应是活动于西汉水流域的白马氐后裔,[18](P10-18)武都、宕昌一带的藏族应是活动于白龙江流域的羌人后裔,他们的民族文化也具有鲜明的氐羌文化特征。
远古时期生活于西北地区的氐羌族群盛行巫傩文化,当地的一些考古实物中,就有巫傩文化因素,部分彩陶文饰就具有鲜明的巫术含义;《山海经》的《西经》部分,也有大量关于巫觋的记载。这种从史前时期就盛行的巫傩文化,其后在陇东南一带民间广泛流传,直至现在,从西北迁居川北的羌人,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巫傩祭祀活动。陇东南一带广泛流传的“羊皮鼓舞”和藏族同胞的“傩面舞”,就是古代氐羌族群巫傩文化的活化石。
白马藏族每年春节举行的大型傩舞“池哥昼”(图6),其源头就是古代氐羌族群巫傩文化。首先,其装饰特征体现出鲜明的氐羌文化特色:主体角色“池哥”身穿羊皮袄,背后用羊皮做成尾饰,手持牦牛尾,头戴装饰雉尾的“三目神”面具,威武神秘。羊皮袄和尾饰应是白马人对羊造型的模仿,源于氐羌人对羊的崇拜。其次,组织形式也具有原始傩舞的特色:在“池哥昼”表演中,四个“池哥”手持法器,和两个“池母”随着锣鼓节奏同时起舞,这种形式虽然经过历代的演变已具有民间社火的特色,但仍保留了古老的巫傩舞特征,这正是群巫同时起舞驱邪的原始巫傩文化形态。最后,“池哥”所戴“三目神”面具,也具有古老氐羌文化的渊源:白马人的“三目神”面具,其文化渊源应是远古氐族的“三目神”崇拜,而“三目神”崇拜又源于氐羌族的“雕题”遗俗。[19](P1-11)所以,白马藏族的“三目神”面具,其实是氐羌族群先祖崇拜的延续。宕昌藏族也举行“羌巴舞”,因舞蹈时头戴怪异的面具,所以也称“牛头马面舞”,一些地方学者认为宕昌羌是由古代牦牛羌与白马羌融合而成,所以视牦牛和白马为图腾。其面具的头顶部位不仅有羊角或牛角装饰,且额头正中也有一纵目,亦为“三目神”面具。可见他们与邻近的白马藏族在文化渊源上有内在关联,他们崇拜的“三目神”都出自远古氐羌族群的图腾崇拜或先祖崇拜。
陇东南一带汉族广泛流行一种祭祀活动“羊皮鼓舞”(图7),也称“传神”或“传爷”,因祭祀活动在巫师迈着舞步敲鼓唱歌中进行,和佛教、道教宗教形式迥异,所以当地老百姓形象地称其为“花儿道场”,其实就是能歌善舞的氐羌部族遗留下来的祭祀形式。其法器羊皮扇鼓,源于氐羌人的羊崇拜。据目前川北羌族民间传说,羌人的天书被羊吃了,羌人受神猴指使杀掉了吃经书的羊,用羊皮绷鼓,敲鼓时就会传出经文。[20]巫师控制着氏族部落的宗教、政治、历史和文化,所以故事的实质是指羌人的文化源于羊皮扇鼓,羊成为羌人文化的本源。羊皮鼓傩舞的男巫师称“师公”,女巫师称“师婆”,男巫身穿长衫,脑后扎一条长长的马尾辫,随着羊皮鼓的节奏迈步甩动,节奏强烈。巫师这种奇特的装饰特点可能源于古代氐羌人的装饰习俗。几个巫师同时起舞唱歌,这种组织形式也与《山海经》中记载的群巫作法进行宗教活动颇为相似。在陇南北部一些地区,当祭祀活动达到高潮时,师公还要用菜刀砍破自己的额头以祀神,这种形式也可能与远古时期氐羌人所谓的“雕题”习俗有关。
陇东剪纸中的“娃娃”,除了单独纹样以外,还有一种二方连续的组合式“娃娃”,俗称“五道娃娃”或“燎疳娃娃”,主要用于招魂驱邪,显然已不仅仅是“抓髻娃娃”的生殖崇拜主题了,其造型、组织和结构特征亦与群巫祭祀形式相类似,应源于古代氐羌的巫傩文化。此外,陇东南一带民间的“杨氏爷”“白马爷”“马王爷”“家神爷”信仰及其宗教造像,也都带有鲜明的氐羌文化特色。总之,氐羌文化既是陇东南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陇东南民间美术独特的审美意蕴形成的重要因素。
结语
秦汉以后,陇东南一带交通枢纽的作用依然突出,早在史前时期就存在的秦陇、陇蜀古道,在秦汉以后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的兴起,使陇东南一带成为中外经济贸易的通道,也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端口。其后,又有南北之间以茶马贸易为主的“茶马古道”兴起,陇东南中部的天水一带曾是茶马贸易的核心地区,[21]而茶马古道同样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陇东南纵横交错,促进了东西南北和中外文化的交融,也不断将不同的文化因素注入陇东南一带的民俗民艺中。其中以宗教美术和民居艺术最具代表性。佛教文化正是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内地,陇东南也是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传播的重要地区,形成了以麦积山和北石窟寺为中心的陇东南佛教艺术群,随着佛教文化的民族化演变,当地民间艺人在创作中遵循宗教艺术程式的同时,也将陇东南的历史文化和风土民俗融汇于佛教美术中,使其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从而形成了陇东南民间宗教美术鲜明的地域特色。陇东南区域地理跨度大,气候差异明显,地形多样化,纵向贯穿西北黄土高原和西秦岭山地,再加上多民族文化的碰撞融合,由此形成结构独特、风格多样、内涵丰富的陇东南民居美术文化特色。陇东南北部的陇东黄土高原一带由原始类窑洞式居室逐渐演变为窑洞式民居;[22]陇东南中部的渭水、西汉水上游由原始地穴式和半地穴式居室逐渐演变为“土墙板屋”式地面土木结构建筑;[23]陇东南南部则吸收南方民居因素,形成了二层或三层土木结构的木楼式民居。
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塑造了陇东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原始文化、周秦文化、氐羌文化、巴蜀文化、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熔于一炉,从而形成了陇东南民间美术历史渊源深厚、艺术类型多样、文化意蕴丰富、区域特色鲜明的地域特色,并且体现出东西南北区域之间鲜明的过渡性特征。陇东南民间美术遍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筑、家具、泥塑、绘画、剪纸、皮影、纸扎、编织、服饰、刺绣、面具、木偶、傩舞、社火、戏曲装饰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民艺,都深受本土文化和陇蜀古道、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文化传播功能的影响,类型丰富,底蕴深厚。这些民间美术以其特有的方式,讲述着陇东南地区复杂深厚的民族历史,彰显着陇东南区域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对这一区域民间美术的研究,既是我们研究和探寻陇东南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契合国家“一带一路”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精神,更是甘肃省“一带三区十三板块”和“向南开放”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或缺的文化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祝中熹.汉渭文化圈与嬴秦的崛起[J].陇东学院学报,2015,(2).
[2]靳之林.论中国民间美术[J].美术研究,2003,(3).
[3]叶舒宪.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J].文学评论,2006,(5).
[4]漆子扬.武山地区史前文化与民问艺术中的伏羲印象[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4).
作者余永红
《陇东南民间美术的历史文化意蕴》
- 花卉园艺论文盆栽花卉养
- 科技改革论文简析邓小平
- 新闻论文发表媒介终端化
- 内蒙煤炭论文发表分析煤
- 电气自动化技术新发展运
- 中国外语教学期刊征稿目
- 液压与气动杂志2016年目录
- 中级科技职称论文范文:
最新优质论文
- 施工技术期刊发论文要求
- 两三千字论文能发核心吗
- cpci是什么领域论文数据库
- 如何让sci杂志延长修稿时
- 中国民族博览是艺术类核
- 评价期刊质量的指标
- 最新!锡林郭勒盟在全区
- 写车床维修论文参考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