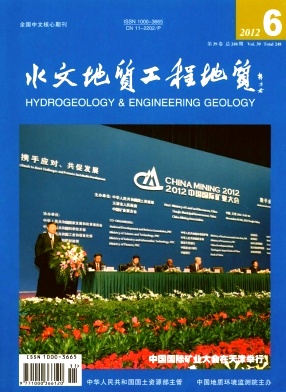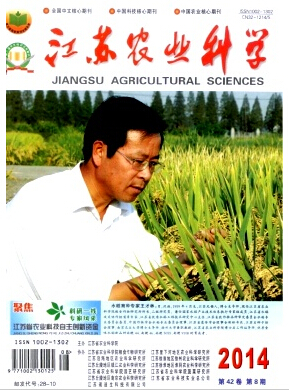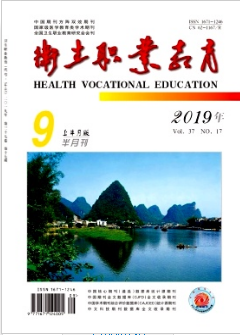从新内涵到新境界——读卢一萍长篇小说《白山》的美学质地

内容提要:《白山》回应重建英雄叙事的时代呼唤,通过执拗素朴如赤子的主人公凌五斗形象的塑造,刷新了对和平年代格式化英雄的认知;小说将荒诞与写实,喜剧与悲剧,戏谑与庄严,幽默与反讽,歌颂与批判,鞭挞与悲悯,谎言与寓言,魔幻的非理性与思辨的理性,这些诸多矛盾与悖反的元素交汇融合,在语言表达和叙事手段上新意迭出,达到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美学的和合圆融境界。
关键词:素朴 写实 魔幻 复调 荒诞 超越
自上世纪90年代先锋作家浪子回头之后,激进的叙事革命和语言实验偃旗息鼓,形式探索的驱动力逐年式微,“写什么”与“怎么写”的价值秩序颠倒过去之后被重新颠倒过来,经历了现代派冲击的亢奋,后现代洗礼的迷惘,阅尽人间春色的作家队伍终于稳住了阵脚,重新集结到现实主义的大旗下,开始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了。
然而挑战层出不穷,迷惘亦并非与日递减,这支队伍在新时代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急速变化的现实生活的难以把握,那些光怪陆离的人生百态及其折射的世道人心,让作家安身立命的想象力相形见绌。近日各大网站频频刊发复旦中文系百年系庆讲坛事宜,一干小说大咖聚首学府谈文说艺,竟至大倒苦水,一言以蔽之曰:“这是非虚构的好时代,写小说却很难”①,肺腑之言,甘苦自知,道出了小说家的深层次困境。
此情此景,情可以堪,对像卢一萍这样“下半生会以小说写作为主”②的作家来说,小说的可能性何在?或者说,小说用什么手段证明自身的价值,来和非虚构争夺生存空间呢?

稍加逻辑推演便可自证:小说只能以其“虚构”来对抗“非虚构”,英语fiction/non-fiction 的文学类别划分,比汉语更清晰地标识了二者的分野。在我看来,虚构不同于再现式非虚构的地方,即在能否兑现米兰·昆德拉确立的价值:“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③;而所谓虚构,还必然包含叙事学意义上的形式美学创新。
这两点庶几可以成为衡估小说家优劣的标准,虽说现实主义强力回归是不争的现实,但是现今的许多作家已经不再拘泥于教科书上经典现实主义的定义,现代主义乃至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技术性手段,得到日益娴熟的运用,不断改变着小说的文本呈现。或许只有把小说《白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安放到这一背景下,庶几方能看出这部长篇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式的操作,甩开了何等遥远的距离。
执拗与素朴:时代英雄的新内涵
对英雄的向往与崇拜是人类亘古不灭的情结,英雄书写遂理所当然地成为军旅小说永恒的主题,说当前军旅文学面临瓶颈,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一领域面对的挑战,因为在这一“永恒主题”漫长的写作史上,先行者已经烙印了各种叙事立场和叙事策略:
神圣化。神圣化是革命文学英雄书写的美学质地,它的来源是革命理想革命信念光芒的照亮。英雄的神圣化是体制文化的产物,人物在作品中的存在带有强烈的被规定性,彼此之间很难有个体差异性形成的区分度,其性格通常只是单一的戏剧化性格(比如英勇顽强和坚贞不屈),并且在冲突中不断趋于强化与集中,主要人物性格有明显的可预测性,甚至基本上可以视为作品的主题性符号,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更为关注的是所指的构成即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乃至于凝固为一种符号化的所指。
平庸化。平庸化是对神圣化的反拨。新时期以降,为了祛除笼罩在英雄头顶神性的光环,我们祭出的法宝是“人性”,试图以人性取代神性,其理论支撑是人物性格的多重组和论,而北岛的一句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则几无异于堵绝了赓续英雄书写的文学之路。彼时文学界盛极一时的潮流是“新写实主义”,以展示小市民平庸、琐碎的“原生态”生活,挑战高大上的意识形态话语,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军旅文学旋即以高唱“农家军歌”回应了这股潮流,此刻走进人物画廊的典型,不再是气壮山河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是披上了军装的农民,他们走进军营怀揣的理想,不是保家卫国建功立业而是寻求出路,是为了摆脱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宿命,为此可以蝇营狗苟不择手段,而最终人物的归宿又往往是悲摧的,当然这种悲摧却并不具备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性,因为它缺乏崇高的支撑。
草莽化。不妨将草莽化视作神圣化与平庸化之间的调和与折中。电视剧《亮剑》热播后,主人公李云龙的塑造,延续了革命文学中英雄书写的底色,却不再采取或不仅仅采取正向叠加的方式拔高人物,而是反向地掺杂了若干农民性格特点或弱点于其中,以此去除神圣化英雄的单一色泽,使人物有血有肉形象丰满,使作品充满了烟火气。这部电影冲撞了被神圣化英雄书写固化了的期待视野,一新观众耳目,“亮剑”竟成为至今使用频度依然很高的流行热词,在新时期文学中极为罕见。《亮剑》的成功引来英雄书写的跟风潮,当英雄人物身上的“反向叠加”元素把握失度之后,英雄草莽化或草莽化的英雄,就蔚成一时风气了。
戏谑化。所谓英雄的戏谑化,或戏谑化的英雄,这里指的是充斥影视作品中,被观众目为“抗日雷剧”、“抗日神剧”中的英雄。这些英雄通常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能变战场如秀场,视敌寇如无物,以至雷人桥段充斥,无厘头情节迭出,真个“神乎其神”。乍看起来,似乎是在延续神圣化英雄书写的脉络,然而此一“神”非彼一“神”,无论是其依托的文化语境、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还是作品的最终呈现,二者的差别都是本质意义上的。
在当前文学界尤其是军旅文学界,呼唤时代英雄,重建英雄叙事是一个热切的话题,而所谓“重建”,自然意味着对上述叙事立场、叙事策略的突破,这个“突破点”应该选在哪里呢?日前多家权威文学机构组织的研讨会上,业内专家达成共识的路径,是“挣脱历史惯性,回到人性复杂的维度塑造英雄”,因为“英雄首先是一个健全的人,然后才是一个英雄”,“人性有多复杂,英雄本身就有多复杂”,因此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呈现英雄身上丰富宽阔的人性”④。这些言说,显然是建立在对革命文学中神圣化英雄叙事反思基础上的,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不容置疑,操作上却难免进退失据:试想倘若以“正向叠加”方式增添“人性复杂的维度”,难免重蹈“高大全”的覆辙;倘若以“反相叠加”的方式,以呈现“丰富宽阔的人性”,则无非是走“英雄+缺点”的老路。两者均很难见出美学意义上的突破。如今,《白山》分明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减法,卢一萍在向我们昭示,重建英雄叙事的路径并不止一条:“复杂”可以是英雄性格,“单纯”不更可以是英雄本色吗?
主人公凌五斗带有几分憨傻的执拗与素朴,刷新了人们对和平年代格式化英雄的认知:参军伊始,军列上便开始了“比工蜂还要忙碌”的劳动;班长恶作剧性质的罚站军姿,他竟能头顶水碗入定为一具模特;主任让他养猪,他能干成“英雄的猪倌”;在一个“没有活着的东西”,唯一的念想就是能“证明自己还活着” 的绝境中,独守高原哨卡半年之久;为了找回战友遗体,像愚公挖山不止,以一己之力“打通天路”;“蹲禁闭”时,“为了御寒保命”,他竟然“不停地小跑了三天四夜” ……
凡此种种,让人想起《士兵突击》中的“另类英雄”许三多来,然而两者只不过具有若干表面的相似性,许三多的所作所为,意在彰显“平凡中的伟大”,仍然属于“正面标准像”之列,可以纳入意识形态话语言说范围,凌五斗的立意却不在于此,至少是不全在于此。这种“一根筋”式的执拗,在浓墨重彩的“假枪毙”一章达到了高潮。在一言即可“前途无量”,拒绝就要埋骨雪山的选择中,凌五斗仍然是个“宁愿被毙也不回头的一根筋”。小说似乎重现了革命文学中英雄人物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风骨气节,落脚点却另有所指。小说扉页援引名言之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曰:“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时,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若我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原来,就凌五斗的心性而言,已经达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境界了,哪怕是将其视为宁死不屈的英雄,用佛家语来说,也都是“着了相”了。这种宠辱不惊的人格,在送别复原离队的徐通时所说的一番话,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我知道我很笨……我就是个只会种地,只想着养几头猪的农民,我其实就想回去陪着我奶奶和我娘,就想回去种种地,让她们每天都有白面馒头吃,再养几头大肥猪,让她们肚子里一年四季有油水。”这段表白看似是地道的农民意识,是“农家军歌”的回响,但是放置在那个“这段时间人世刚好在发疯”的背景,放眼周遭上下,无不出于个人功利心的对凌五斗的塑造,这份朴素与真情,这种对“普通”的追求,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卢一萍笔下的凌五斗,还不仅仅是农民式的本分,在钱排长眼中,“凌五斗的眼睛那么纯洁天真,跟儿童的一样”;在指导员傅献军眼中,“他看到凌五斗的目光那么清澈,像婴儿的一样”。这使我们想起老子“智慧出,有大伪”的感叹,而摆脱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遭受污染的途径,则是“复归于婴儿”,可以说,这也是卢一萍的人格理想。可是怎样才能复归于婴儿呢?不同于老子的“弃圣绝智”,卢一萍划出的底线是“说人话”,在那个“整体的谎言……个体的谎言,二者相互支撑、勾结……支撑着人类”的时代语境中,他借助黑白猴子的愤激之词说;“人话本来就是神仙的语言……你们把它糟蹋得连人话都不是了”,仅仅是因为凌五斗嘴里说人话,才使他成为“离天使最近的人” 。彼时彼刻,“神话” “鬼话” 弥漫,“人话(实话)” 成为“实(人)话病”,朴拙与素朴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珍贵和稀缺的元素;此时此刻,情况如何?小说时间下限限定了,没有说,没有说不等于没说,优秀的小说可以超越时间,“人离天使最近,但离魔鬼也近”,我们分明可以窥见文艺复兴时期先哲前贤的理想,在卢一萍心头的照亮,让人升腾为天使,不要堕落为魔鬼,这就是凌五斗给我们的启示。
丝不染为素,木不雕为朴,凌五斗的坦荡和磊落,就是一匹未染之素,未雕之木。这一形象使我想起罗丹对什么是雕塑的著名回答:砍去多余的部分。卢一萍剥离了加在英雄人物身上的许多“多余的部分”,如同罗丹砍去了巴尔扎克雕像上那只众人赞叹不已的手。
写实与魔幻:人物塑造的新手段
细节的真实性,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些被现代主义弃若敝屣的陈规,是经典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白山》对这些原则或遵从或背离,或写实或魔幻,缠绕扭结,形成一种别样的文学景观,落脚点却在服务新人的塑造。
所谓典型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外乎是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组合。《白山》锁定的主要时间段,是上世纪70年代(接近尾声时甚至借助书中人物的一份文字材料,点明了大致的下限: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小说划定的场域,是雪域高原世界屋脊,捎带内地一处穷乡僻壤。不同于现代主义往往虚化时空以求小说的寓言性,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指涉,通常是现实主义写实手法的一个显性标志,在中国这个社会生活阶段性特点十分明显的背景下,这一标志无疑显得格外重要。
写实玩不得花架子,指靠的是27年军旅生涯和请缨世界屋脊的生活积累;魔幻则不能拘泥于脚下,仰仗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70后作家的教育背景为之提供了飞腾的助推剂。
卢一萍笔下的雪域高原,有时候是圣洁瑰丽的,有时候是狰狞恐怖的;圣洁瑰丽是主人公心灵的映照,狰狞恐怖是主人公精神的淬火。可资佐证的是,外在的山水,常常是通过凌五斗的注目和感受,以主观镜头方式呈现的:
“那些沉睡、凝固了的群山被那一轮圣洁的月亮重新唤醒了。他感到群山在缓缓移动,轻轻摇摆,最后旋转、腾挪、弯腰、舒臂,笨拙地舞蹈起来,还一边舞蹈,一边轻声哼唱着。”
雪豹、棕熊、猞猁、黑颈鹤、斑头雁……紫花针茅、垫状骆驼藜、青藏苔草、冻原白蒿……这些内地人陌生的动植物扑面而来,在细节上填充了人物活动的疆域,令人想起“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的夫子之训。
所谓社会环境,不过是人类活动的集合。不言而喻,通过特殊地域特殊人群,即雪域高原乃至于生命禁区中为数不多的军人活动,传达出来的社会氛围毕竟是有限的。小说的技术处理,一则是通过边防连的层层上级对下级的掌控,从纵向延伸,二则是通过凌五斗口头禅般“在我们老家乐坝”的絮叨,从横向铺开,于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便化为弥漫于全书的一种氛围性的存在了。
即便如此,上述手法仍然属于常规性手段,变异仅仅出现在主人公以及与他紧密相关的两只小猪的描写上,魔幻的变形与细节的逼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倒车镜里的家伙骨瘦如柴,军装又脏又破,结成股的长发披肩,凌乱的大胡子已经垂胸,面孔红紫,眼窝深陷,颧骨尖削,乌紫的嘴唇连门牙都包不住了”——这个“的确像个鬼”的人,就是绝地独守孤哨半年的凌五斗,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的肖像画立于读者眼前,给人以深深震撼。然而我们又看到,凌五斗因为对伟人像评头论足而被批斗三天并从台上摔下而伤及大脑,此后即不会说谎了,并且“好多话都会奇怪的应验”;在海拔5300米的天堂湾,能“跑得跟风一样快”,而且过目不忘,能将五卷雄文横流倒背;“比别人抗寒,有时候饿好几天一点问题也没有”;为了护卫倾心饲养的两只小猪黑白猴子,他“像一尊金刚”,“像根系深深扎进大地深处的老树桩”,任凭一群战士冲上去,也“像是和整座高原焊接在一起了”而“纹丝不动”,此后则通体变蓝,被美国之音和塔斯社称为“蓝皮肤的外星战士”,中国“有可能借助其超凡的能力来征服世界”;而为了一睹蓝色“外星战士”风采,边地城乡万众奔走的场面,则构成小说浓墨重彩的章节;黑白猴子肉体变成饺子馅,灵魂却化为天使,和凌五斗倾心交谈……
若问,作家何以要赋予笔下的主人公种种“超凡的能力”呢?倘为了玄奇猎异,则远无法和时下大热的玄幻类、穿越类网络小说争锋,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考”⑤,采取以人物原型为模特,或杂取种种的传统叙事策略,显然无法突破给英雄人物照“标准像”的陈规,无法抵达“对存在进行的思考”的深度。
凌五斗这一形象的确立,不仅如某些论者所言,扭转了眼下许多小说有故事无人物或重故事轻人物的时弊,更重要的是澄清了人物塑造上的一个误区。无需多少文学理论便可推想,如果说短篇小说可以以性格单一的人物作主人公的话,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若作如此操作,是会冒很大风险的。自从福斯特提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这两个概念以来,轻前者重后者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倾向,尤其是刘再复提出“性格组合论”,林兴宅以系统论解读阿Q性格的多重组和,更使这种倾向左右了长篇小说的人物塑造。《白山》基本上是以线性展开的情节,不断强化着凌五斗的单一性格,这使我们重新记起福斯特对扁平人物有一是容易辨认,二是容易记忆这两大长处的论断,也使我们要向中外文学史中那些著名的扁平人物致敬。
复调与荒诞:观照世界的新眼光
凌五斗的父亲是一个解放战争中牺牲在青藏高原的英雄,父亲骑红马在白色雪山“郁郁而行”的画面,无数次出现在凌五斗的梦境里,成为贯穿小说首尾的意象;回应父亲冥冥中的召唤,凌五斗入伍戍边,来到父亲当年战斗的世界屋脊,在“白山”摔打磨炼。
凌五斗原是以烈士遗孤身份,被更改年龄,隐瞒已婚身份方得以入伍的,机缘凑合,新兵入伍军列上即被军区报社记者报道表扬,此后各级领导出于政绩需要,“通过轮番、立体、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攻势,一步步将其打造成“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参与者亦各有升迁。
倘若着眼于前者,这便是一曲继承先烈遗志,戍守生命禁区,彰显奉献精神的赞歌,是一种虽显老套并高度意识形态化,却仍不失其价值的英雄叙事,似乎可以纳入神圣化英雄之列了。
倘若着眼于后者,便可视作对“先进典型是怎样炼成的”大揭秘,原来那不过是上级“高瞻远瞩”,不惜以“兵不厌诈”手段“培养”起来的,如指导员傅献军那句一针见血的内心独白,“所谓树立先进典型,是属于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特产,它是把一个行业、一个集体、甚至全国人民做的好事放到一个人身上,让它充满神一样的光芒,以便人们仰望和学习”,如此这般,小说的基调便显然是讽刺与批判。
不难看出,倘若以巴赫金给出的复调理论评判,《白山》或许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复调小说,因为它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那样,不同“声部”不在作者的统一意志下展开因而得以形成对话关系,无论言颂言刺,都是《白山》作者对象化的存在,都浸润着作者的悲悯与大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将其视为一部复调小说,因为作者不露痕迹地将歌颂与批判赋予了各自的平等性,而整体上又具有不可分割性,横看成岭侧成峰,取任一角度把握《白山》的叙事伦理和价值取向,都是持之有据言之有理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两种取向是互不兼容,彼此拆解的,前者可谓之“真英雄”,后者可谓之“假典型”,孰真孰假,凌五斗到底所系何人,小说似乎同形式逻辑的基本思维规律开了个玩笑。
个中奥秘在于,“真英雄”也好,“假典型”也罢,这只是旁观者的眼光和立场,于凌五斗本人却并无多大干系,小说扉页所题的三段名言,是作者精心挑选的解读小说、解读人物的钥匙。其一曰“宇宙由三重境界组成:上为光明,中为风,下为尘土”。作者从藏传佛教密宗的世界模式图中得到启发,借此搭建了小说构架:主人公凌五斗自“癞蛤蟆”始,历经外界包装(这又是他磨炼、修为的过程),最终成为“蓝色士兵”、“外星战士”和“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二曰“我要生活在历史之外”:“孤悬人世之外的雪海孤岛上的战士”,是“生活在历史之外”的表层意涵;于举世浑浊中而皎然不滓,是“生活在历史之外”的深层意涵。凌五斗在对天使提出心中的愿望时说:“我想做一个普通士兵。”天使的回答则是:“你本来就是个普通的士兵,只是比很多士兵还普通而已。也就是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你还有怎么个普通法?”在我看来,这正是这部小说英雄书写的标新立异之处。也正是凌五斗这一形象独立特行,判然区分于以往军旅小说人物的地方。
我之所以将《白山》成为复调小说,还因为其中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世界。当凌五斗“赶着马儿从喀喇昆仑的大荒之境进入了至纯至美的王国”时,作者便调动诸多艺术手段,以抒情诗的语言,浓墨重彩地铺排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人与动物植物和谐相处的香格里拉:这里“金色的草地漫无边际。那是纯金的颜色……险峻的冰山像是用白银堆砌起来的……天空的蓝显得柔和,像安静时的海面……这里的每一座峰峦、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都皈依了佛……高原如此新鲜,似乎刚刚诞生,还带着襁褓中的腥甜气息;大地如此纯洁,像第一次咧开嘴哭泣的婴儿”。在这个神山圣域中,牧羊女德吉梅朵踏歌而来,这个清纯的未被红尘污染的自然之子(女)及其生活的世界,与同样清纯的凌五斗的内心世界契合了,这个世界与那个充满虚伪、算计甚至暴力的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德吉梅朵藏语中为“幸福的花儿” 之意,作者的倾向性显然是隐含其中的。
对另一个价值世界的观照,是洞穿其荒诞性。如果说“伤痕文学”的痛定思痛,是以悲剧的眼光阅读历史刚刚翻过的一页,“反思文学”的思考追问,是以正剧的眼光寻求历史的答案的话,当卢一萍回望那段历史时,一则拉开了相对遥远的距离,二来经历了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美学的陶冶,他便得以用不同于前辈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当代史上那梦魇般的十年。
西方现代/后现代美学有一个核心概念,谓之“荒诞”。和几乎处于西方美学源头,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进行了经典性论述的悲剧、喜剧比起来,这一概念及其依存的创作实践的产生,不过是20世纪中叶的事情,这一美学概念的巨大意义,在我看来,是在悲剧、喜剧这一对基本的美学范畴之外,又开启了艺术把握世界,探讨人类生存状态的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无疑给了卢一萍深刻的美学启示,成为《白山》叙事的底色。
荒诞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揉搓着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于那一对猪崽,从平原腹地的乡野,到雪域高原的军营,无论是悲是喜,是荣是辱,皆裹挟其中,无可逃遁。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而“祸从口出”,可以整死两条人命,也可以让堂堂军医“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公社革委会主任可以“每个大队都有相好”,“别人有相好那叫男女作风问题,他有相好那叫革命工作需要”;“我国最权威的养猪杂志”,是《社会主义养猪业》,专家之间的笔墨官司,是争论“用资本主义的东西来研究社会主义养猪业是荒谬、荒唐的,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猪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猪是反动的”……
过来人都会知道,上述种种,并非作者刻意为之,而是高度写实的。当变态的社会生活已然成为常态,沉浸其中的人们是不会有荒诞感的;《战胜报》何记者从写凌五斗第一篇报道,“就开始转运了。不到三年,她把凌五斗从一个新兵塑造成了一个全军区闻名的典型”,“军区的首长们已多次看到过有关凌五斗的报道,觉得凌五斗已入伍三年,作为一个典型已经培养成熟,决定将他树为‘世界屋脊上又红又专的钢铁战士’,列为明年的重大典型,重点宣传,先推向全军,继而推向全国”……
这些不露声色的平直的叙述中,同样可以咂摸出内在的荒诞味来,但它同样是高度写实的,对非过来人的一代读者,就不一定能体会其间的荒诞了。这提醒我们,荒诞的内容需要用相对应的形式来把握,这或许就是贝克特、尤奈斯库、马丁·艾思林等荒诞派大师留给我们的启示,当然说到底这不过是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美学常识罢了,困难不在认识,难在认识之后的操作。
正如诸多现代派绘画带给人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是其变形而判然有别于传统绘画那样,《白山》荒诞叙事同样离不开变形,而以文字为传达手段的小说的变形,一是借用夸张,二是借用魔幻。
当我们将荒诞作为与古老的悲剧、喜剧并列的一种现代的审美范畴看待时,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荒诞的审美效果,通常是悲剧和喜剧因素的融合而得以显现的,《白山》的叙事印证了这一点。
卢一萍是一个富有幽默感和喜剧才华的作家。凌五斗身上,便可以窥见好兵帅克和那个“智商只有007”的憨豆的影子,通信员汪小朔和文书温文革一对活宝,性格反差很大,着墨不是很多,行文却浸透了老道的幽默和嘲讽,给小说增添了许多喜剧色彩。“文书的文采,按他自己的说法,在世界屋脊也是数一数二的”;汪小朔的插科打诨信口胡诌,则放大了荒诞性喜剧性,他在向检查团介绍养猪经验时,完全照搬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说教,比如“人需要精神,将心比心,猪也应该需要的”,所以一日三餐喂食前,“各灌输一次”,启发“有幸来到海拔最高哨卡的两头猪,应该感到无上光荣和无比自豪”,教导它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除此之外,“还常常给它们讲我们连队的光荣传统”,讲战士们“在这里生存、生活、执勤、战斗时发生的感人故事”,而终于“潜移默化”,“还真起了一些作用”,“高山反应很快就变轻了”,猪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明显的好转”。当我们看到“科学家”面对母牛的胡说八道一本正经地“听得很仔细,几乎一字不漏地记录着”,也声言“相信精神的力量”,并且“从动物学研究”的专业立场,称赞“这是一个新的观点”而英雄所见略同,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印证的例子”,而今不虚此行不能不万分激动以至于“热泪涕零”时,甚至当原猪“黑白猴子”意外现身,假戏穿帮之际,竟“更倾向只是一个新物种”时,都会产生忍俊不禁的阅读效果来。正是忽悠检查团和戏弄凌五斗这两场戏,把小说的荒诞性和喜剧性推向了高潮。
高干子弟孙南下和排长钱卫红,是两个悲剧性人物。作者在描写这两个人物(还有连长等人)时,可以窥见精神分析学的影子在其间晃动。孙南下的特殊身份,在连队里“与其说他是个兵,不如说他是个爷”,因为自我期许甚高,而凌五斗取代了理应被“树为先进立为典型”的自己,以至于心理失衡,这个“受父母的影响,是个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者,连鬼神的影子也不信的”人,居然被吓死了;钱卫红则是性心里的压抑,通过自我阉割以求解脱,是那个 “存天理灭人欲”扭曲人性时代的牺牲品,作者借黑白猴子的“天使之言”,道出了被荒诞的意识形态遮蔽的简单的人生道理。
抵达与超越:长篇小说的新境界
描绘一个时代的风俗风情,展示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用巴尔扎克的表白,就是做书写社会历史的“书记官”,如此就抵达了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的目的地,如果这部小说所写为军事题材,按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概念,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纳入军事文学范畴言说了。
日前在成都举行的《白山》首发分享会上,跻身著名军旅作家的卢一萍却坦言:“我不太承认有军事文学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军事文学这个概念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分类的,比方说分为军事文学,煤炭文学,国土文学,还有海洋题材,森林题材,分了很多类。”⑥评论家王龙深谙卢一萍的文学野心:“他写军队的历史往事,但又坚持一定要超越职业、题材、历史、甚至国别和民族。”⑦这些言论足以说明,理性已经深深渗入到70后这代作家群的创作中。
超越性的有无,正是衡估一部作品是否跳出了行业化、类型化等诸多狭隘圈子,真正具备了美学价值的评判尺度。在我看来,《白山》在人物塑造和形式探索,亦即通常所说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兑现了他追求的超越性。
“浑身冒着傻气”的凌五斗,使我们联想起他的许多前辈来。傻瓜类型繁多,在巴赫金看来,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早在荷马时代,《伊利亚特》中就有一个敢于嘲讽统帅阿伽门农的“军中傻瓜”忒尔西忒斯,但是比较起来,俄罗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傻瓜伊凡》,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英国电视剧《憨豆先生》,美国电影《阿甘正传》,这些广为传播的作品里的主人公,和凌五斗有更近的血缘关系,通过傻瓜形象传达一种对时代的价值思考,以及喜剧精神和批判精神,是这类作品的共性,至于他们的身份是军人还是平民,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圣经》有言“上帝保佑傻瓜”,民谚则曰“憨人有憨福”,足见凌五斗的讨人喜爱是超越时空的。
《白山》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对形式美学的阶段性跃迁上。
虽说现实主义强力回归是不争的现实,但是现今的许多作家已经不再拘泥于教科书上经典现实主义的定义,现代主义乃至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技术性手段,得到日益娴熟的运用,不断改变着小说的文本呈现。或许只有把小说《白山》安放到这一背景下,庶几方能看出这部长篇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式的操作,甩开了何等遥远的距离,在这部小说中,内容与形式已经达到高度的契合,作为小说支撑点的“荒诞”,与西方原始意义上的荒诞,已经有了许多根本性质的不同。首先就语言层面上看,荒诞派作品的语言往往是跳动的,晦涩的,能指与所指常常是分离的,这给阅读趣味为传统文学培养起来的读者造成很大的不适感,就像习惯了欣赏古典美术“高贵的端庄和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语)的眼睛,突然接触到毕加索、马蒂斯受到的冲击力那样,反感和排斥几乎是必然的反应。《白山》的语言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僵硬的文革语言与纯美的诗化语言之间的张力,形成别样的文本呈现。前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话语体系,时过境迁,在“后革命时代”读来,便徒生出滑稽感来,这也是不同于西方黑色幽默的“中国特色”;后者则更多的出现在白山独特的地域风景的描写上,意向性、象征性是文字背后传达的美学意蕴。再深入一层,荒诞派依存的存在主义哲学津津乐道的主题,是对人存在价值和目的的怀疑,是人被遗弃于一个异己世界的孤独感、陌生感,以及由此滋生的空虚感、绝望感。表面看来,《白山》在许多地方貌似逼近了克尔凯郭尔、萨特和加缪,但是其基本的精神取向却是异质的。简言之,《白山》展示的荒诞,并非是人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类的存在面对的荒诞,更多的是极左政治下现实生活中的悖谬;西方的荒诞叙事务虚,侧重形而上,取全人类视角,其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是宗教信仰、彼岸情怀,它并不以某种具体的价值事物为否定对象,因而其否定是根本性质的,立足点是非理性的(虚无主义的);《白山》的荒诞叙事却务实,侧重形而下,取中国视角,其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是世俗追求,此岸情怀,以具体价值事物的异化为否定对象,其否定是建设性的,立足点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若问《白山》作为小说美学的价值,一言以蔽之,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面对强势的西方现当代文学,已然完成了“引进(翻译介绍)——模仿(移植克隆)——吸收(传达手段)——内化(内在精神)”的阶段,与现实主义融会贯通,达到了不再可以用某种“主义”清晰标定的和合圆融境界,往大里说,再次彰显了中国文化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超强生命力。
注释:
①复旦中文系百年系庆讲坛:《这是非虚构的好时代,写小说却很难》,澎湃新闻2017年12月7日。
②⑨卢一萍:《一直站在表达的中心》,《成都日报》2017年11月26日,第5版。
作者吴平安
《从新内涵到新境界——读卢一萍长篇小说《白山》的美学质地》
- 职称论文刊发主体资格的
- 政法论文浅析工会法主体
- 化学在初中教学中的情感
- 中学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方
- 法治论文投稿法治型市场
- 杂志社论文发表浅析推动
- 新疆教育报投稿浅析学生
- 分男女招生录取的合宪性
最新优质论文
- 舞蹈的地域特征论文发表
- 水文水资源观测论文发表
- 论文发ei需要润色吗
- 论文转投是什么意思
- 科学管理研究是评职称认
- 安徽体育科技发表论文要
- 医学论文投英文期刊怎么
- 经济全球化退与进论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