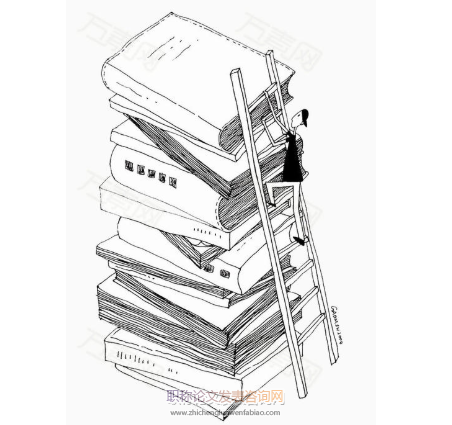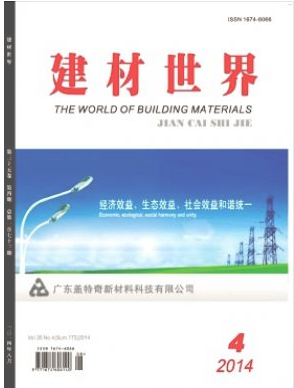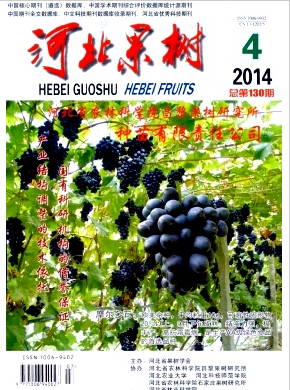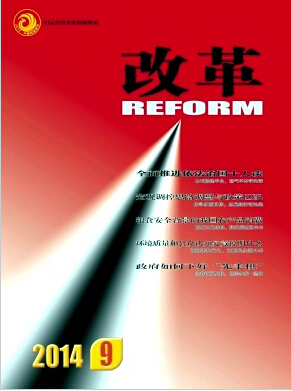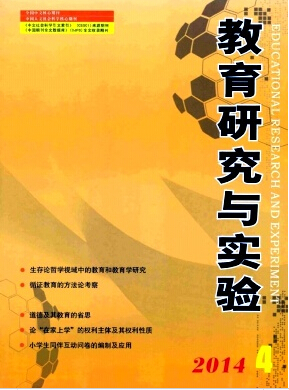摘要:内容提要:19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并非游戏历史的恶作剧,在创伤书写之中,新历史主义小说完成了对古今伤痛的双向解构,伴随而生的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历史虚无,在历史虚无的
内容提要:19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并非“游戏历史的恶作剧”,在“创伤书写”之中,新历史主义小说完成了对“古今伤痛”的双向解构,伴随而生的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历史虚无”,在“历史虚无”的笼罩之下,新历史主义小说藉由“想象历史”的方式,追寻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得到“虚构”与“轻逸”之美,实现对历史的“举重若轻”。故此,将19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视为“游戏历史”的急就章,恰恰是遮蔽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所根植的百年中国沉痛历史之文化语境,更是遮蔽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对一种真实的“创伤文学”、“治愈文学”的历史诉求。
关键词:创伤 解构 历史虚无 新历史主义小说 1990年代
一、引言
长期以来,新历史主义小说1990年代之转型的评价问题似乎已经尘埃落定,论者往往将之归于游戏化历史倾向和历史虚无的一端①。即认为这类创作违背了重建历史观反击历史霸权的时代使命,从一种“先锋”的开拓进取的姿态沦为了历史的虚无主义和价值的虚无主义。②学界对“新历史主义小说”转型的批评确有其证,甚至说这一转型走向了“历史的虚无主义”,也不是捕风捉影。但是回归到文本之中,可以发现,其表面上的“历史虚无”却伴随着难以穷尽的“创伤书写”。故此,旧有的定于一尊的研究范式已经难以涵盖新历史主义小说转型之深刻原因,唯有超克原有的简单化的研究范式,借用“创伤批评”的理论资源,进而站在“时代转型”和亲历历史之人的“个体维度”之上,方能重新认识这种“历史虚无之转向”,从而避免归于冷冰冰的简单化批评。一方面,进入九十年代之中国,启蒙话语已然是被遮蔽的“难言苦衷”,“情理激荡”③推动的启蒙思潮声势浩大却归于一种悲哀的境地,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逐渐转向了另外的一端,后启蒙时代的来临,人们追逐个人的话语追逐个人的小我,不再关注那些公共的话语体系,充分自由的个人化历史写作即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何尝不是满目疮痍,苦难历史所遗留的伤痛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每一个关心历史与现实的人们,何时能从“创伤”的幽影之中解脱出来?这是世纪末的重大难题,“新历史小说”作者们选择“游戏”于历史的素材之中,未尝不是抱有这样一种期望:在汇集历史之创伤记忆的基础之上,进行一次彻底的解构历史、消解历史的“创伤书写”,在历史的虚无之中达到一种对“创伤”的解脱。正在“创伤”这一中间物的基础之上,讨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转型,方可深入历史的幽微之处,才能发掘这一转型的真正缘起及意义,从而重新认识这作为表象的“历史虚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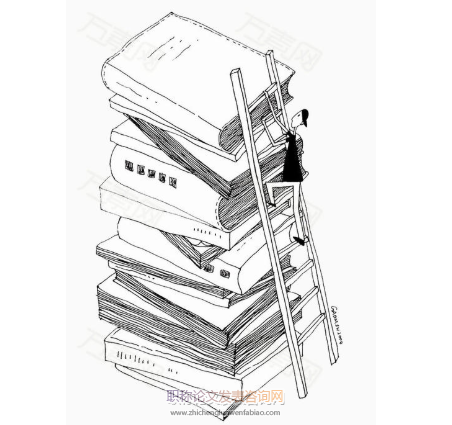
二、“创伤书写”:古今的双向解构
正如库尔兹所言,当代社会的创伤意识在日渐增强,“《创伤与文学》‘导论’中引了《纽约时报》的一组数据:1851年到1960年这一百多年间,‘创伤’(trauma)一词现身该报的次数共计300次;而1960年至2010年这五十年间,‘创伤’一语亮相该报的次数达到了11000次”。④凡是有志于返回历史现场的人,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创伤是历史的一种必然”。⑤而文学恰恰是“重返历史”的重要媒介。文学作品中的“创伤书写”常常以“创伤见证”⑥的现实主义乃至非虚构的创作进行,“直面和书写这种人道灾难的重要文学类型之一,⑦就是‘幸存者文学’和‘见证文学’”, 如《随想录》(巴金)、《思痛录》(韦君宜)等一系列作品都属于此列。而文学毕竟仍是艺术,“见证文学”的限定未免过于狭窄,“创伤记忆”多存在经历灾难的幸存之人,但是作家仍可凭借文字、影像和想象与之同呼吸、共命运。“随着见证者和亲历者的日渐衰老或离世,共同记忆会被越来越快地冲淡及模糊,变得不那么‘共同’”,但是记忆的河流并不会断裂,“记忆的主体承载着各自的使命也在永恒地演绎着生命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责任实践和完成自己所担负的记忆使命”。⑧也即是说,即便“创伤记忆”只属于少数人,但是“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民,都与我有关”⑨,每一个人都应当为延续“记忆”做出努力,在这之中,作家就必然要占据重要的位置,以此研究理路方能从整体上把握“创伤书写”的心理依据和历史根由。在这个层面上,转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进行了有别于“见证文学”的“创伤书写”,“新历史主义小说”并不简单地对伤痛进行文字地复刻,而是在古与今的历史长河之中来回穿梭,寻找历史之中的“共时性”,“在一角一隅、半鳞半爪中让人感知其沧桑变迁、世事轮回”,⑩并最终完成了对古今创伤的双重解构。
在新历史主义小说那里,历史是一条“创伤”积累的河流,历史是一卷为“欲望”的杀戮史。苏童小说《米》的创伤书写就很全面,小说开头,五龙是以受了洪水灾害的难民形象出现在城市里,先是被码头的地痞阿保侮辱,违心地叫阿保为爹,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之中,五龙首先丢失的就是自尊。洪水和饥荒带给五龙的精神创伤是难以餍足的对米的欲望,“食”与“性”总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五龙“性”变态的一部分原因要归于此。“城市人”、“地痞流氓”对五龙的恐吓侮辱则导致了他“睚眦必报”和“阴郁偏执”的变态性格。更为可怕的是,本身作为“创伤”之受害者的五龙,在时机成熟时会将“创伤”十倍加于敌手乃至于身边的无辜之人,一封告密信便令阿保葬身鱼腹;策划爆炸,将六爷的豪宅炸成废墟而置织云于不顾;强奸高傲而冷漠的绮云;因染上性病杀戮八名妓女,逼迫乃芳回娘家生育,导致其被日本兵屠杀。围绕这个人物,整个作品对“创伤”的描写便清晰可见,一个充满苦难与不幸的“悲惨世界”即彰显在眼前。
苏童的《武则天》似乎是要彰显这样的事实:在权力斗争之中,唯有纯熟使用最冷酷最无情手段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欲望”,而历史不过是记载了为这些欲望互相杀戮的诸多事件而已。武照为了在与王皇后的宫斗之中取胜,不惜亲手杀死亲生女儿。在武照通往最高权力的路上,王皇后和忠臣长孙无忌固然是障碍,他亲生的儿子太子贤、太子哲竟也是她的障碍。这一切无不彰显着正统的史书之上所叙述的仁义道德,也不过是“吃人”二字。苏童的另一部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试图以子虚乌有的“燮国国王”荒诞的一生,来象征帝王将相之史,昏君端文当道,却是“太后”为了维持自己垂帘听政局势的幕后操作,“我”的帝王生涯以寓言的形式揭示了这样一个处境:无论是帝王,还是平民,终究躲不过伤害与被伤害的宿命,逃不出杀与被杀的命运。
于是伴随着这“创伤”之河、“欲望杀戮史”而存在的既是升斗小民之流的悲哀无奈,也是一代人在历史天空下体悟到“历史循环”和“宿命”之后的空虚和无奈。《故乡相处流传》里,无论是“在曹丞相身边”还是“六零年随姥姥进城”,延津人民逃不脱强权控制下被奴役、被杀戮的悲惨命运,千年之前是白石头白蚂蚁,千年之后仍是白石头白蚂蚁,即便孬舅在六零年时代当上了村支书,也不过是变成了一个剥削普通人的小头目。面对这样沉重的历史伤痛,无言相对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表达,也难怪刘震云在书中结尾写道:“我年仅两岁,像望着一片永远割不完的一望无际的麦田一样,嘴里竟无师自通地骂道:‘妈的!’”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之中,存在的都是黑暗、腐朽与堕落,面对这样多灾多难的沉痛历史,一代人在愤懑、笑骂之余走向了历史消解之后的虚无。
王小波的《万寿寺》这样表达历史观:“所谓老佛爷,不过是个黄脸婆子。她之所以尊贵,是因为过去有一天有个男人,也就是皇帝本人,拖着一条射过精、疲软的鸡巴从她身上爬开。我们所说的就是历史,这根疲软的鸡巴,就是历史的脐带。”在这类的表述之中,历史简单化、虚无化了,或许有些论者论证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游戏化正是从这类的表述谈起,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之中也有过类似表述:历史本来很简单,是我们把它搞复杂了。除此之外,“历史疲惫、瘫软,而且面色焦黄,黄得就像那些陈旧的纸张一样”,一种反感厌倦的情绪萦绕在其中。在《红拂夜奔》中,王小波想要探讨有趣之于人生的必要性,却在结尾写下: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相信我是对的,就是人生来有趣,过去有趣,渴望有趣,内心有趣却假装无趣。也没有一件事能证明我是错的,让我相信人生来无趣,过去无趣现在也无趣,不喜欢有趣的事而且表里如一。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
面对历史,在“正统”和“光明”被消解之后,在至深的痛苦和压抑之后,一个新的历史也只有是如此“无趣”“悲惨”和“血腥”的循环。由此,一种解构逻辑尽头的“虚无”就开始呈现它的魅力,在这种历史虚无之中,纷繁复杂的矛盾可以得到一种缓解,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伤叙事起到了情感宣泄和修复创伤的作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作者们将古今伤痛揉为一体,在历史简单化的循环之中,人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所经历的难以解脱的灾难和伤痛,在近古、中古那里近乎消解了自身的独立性。因此,这种对历史源流发展的虚无之感,一定程度上促使古代和当代伤痛完成双向的解构。在了然历史的特质之后,在了然历史不过如此之后,二十世纪堆积而来的历史伤痛也可以暂告消解,不再成为一个十足难题,人们终于可以试图甩开沉重的历史幽灵,拥抱大众文化的滚滚潮流,轻装上阵迈向新一个历史时期。
三、描绘“历史虚无”的图景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伤书写”最终导向了古今“历史创伤”的双向解构,而“双向解构”的复杂性便在于,其一方面实现了“创伤书写”的重要功能,起到了情感宣泄和创伤修复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导致文本中的人物愈加“虚无缥缈”,使文本成为远离现实生活的虚构。无论是“戏仿”、“游戏”还是“狂欢”之类的批评指涉,都试图揭示“新历史主义小说”转向“历史虚无论”的重要事实。作为新历史小说90年代转型的核心特征,有论者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藉借反讽方式,使原属合理的行为遭罹游戏化的袭击”,“‘新历史主义’小说甚至拒绝相信历史理性的运作,致使历史结局的必然性常常遭其冷遇。”若要更深入了解新历史主义小说何以“虚无”,仍需探讨这种游戏化的核心特征所具备的特点,并籍由文本的分析探讨“虚无”之表现。“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此次转型恰恰是由相对合乎理性逻辑的“家族史”、“近现代史”、“野史”转向了一种历史与当下共在的大杂烩,通过反讽的艺术逻辑编织起一张亦真亦幻的古今传奇之网。“新历史主义小说”凭借“游戏化叙事”所构建的“历史虚无”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古今杂糅的“时空混乱性”,古代、近代和当代混为一体,小说叙事并不追求历史的逻辑理性,常常是导弹、费马大定理同时出现在历史场景之中,正如论者所言:“虚无主义的原始含义就在于对现实的否定本身”,新历史主义小说正是在古今杂糅的时空之中完成了“怀疑”和“虚无”的第一步。其次是“反讽和戏仿”,通过模拟一些当代人熟知的话语体系,将之置于历史的叙事空间之中,形成逻辑上的反差,从而令人会心一笑,正是这种“个人立场之上对历史进行全新的个人化解读乃至戏谑地反讽”,“在解构霸权历史叙事的快感中突显‘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历史本真与深厚感性,”最后,历史归于“偶然的‘不确定性’与‘可怀疑性’,它们迷离飘忽,若有似无,如历史的迷雾和‘遗案’样难以把定”,对历史动因的追逐陷入一条死胡同,“新历史主义小说”写作者们不再去追逐“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传统情怀,反而陷入对历史深深的质疑之中。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并且“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解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做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的操作”。由此观之,在小说和历史的互动之中,新历史主义小说之走向一种怀疑性的“历史虚无论”有其理论根源。文字记载之历史在写作者那里不再值得敬畏,恰恰因为历史的传承逻辑本身就具有“文学”、“小说”的虚构笔法。
刘震云所写《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即可作为这种转型的一个例证,在《故乡天下黄花》中,人物还有合理的历史逻辑,孙、李两家近百年的仇杀被当作历史时期的典型来写,人物命运几番颠倒,不是孙殿元被李家所雇杀手勒死,即是李老喜被孙老元派来报仇的许布袋吓死,这种夹杂着权力、金钱和性的杀戮在小说的百年时空中反复上演,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文革”时期。然而这一切形式到《故乡相处流传》就大有不同。首先是历史叙事的“时空混乱性”,虽然事件的地点都是发生在延津这个地方,故事却分明写了四个时空的事情,起标题为“在曹丞相身边”、“大槐树下告别爹娘”、“我杀陈玉成”、“六零年随姥姥进城”,分明指涉了官渡之战、明初人口大迁徙、太平天国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四个时期,但是这其中的人物却是互相勾连、古今一贯的,如曹成、袁哨、孬舅、六指、我、白石头、白蚂蚁等人物反复出现在各个时期,因此整个的叙事近于古今杂糅。比如小说中朱元璋为了鼓动猪蛋迁徙延津:“朱也犯了愁,最后拍了一下巴掌,说你先去,等成了财主,再派轿车或雇一个直升机来接她。”再如:“八个洋人一齐站到山上,发了八个巡航导弹,导弹分别落在追赶的队伍中、大本营城里、县衙、村庄、田野、河流等等,把我们延津的人民和土地炸得面目全非。”显然,在明初不会有轿车和直升机,也不会有巡航导弹,这些超时空的物品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文本的荒诞性。文本中像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此又证明了作者已不在意历史叙述的合理性,反而去寻求一种历史即当下的混淆之感。其次,大量的反讽和戏拟之笔令人忍俊不禁,迁往延津的人十成死了七八成时,朱皇上训话:“这是好事吗?当然不是好事。这是坏事吗?我看也不尽然。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一切都好时,大家一盘散沙;一遇到大的困难,反倒增加了凝聚力。”作者显然是带有讽刺意味地令现代人惯用的政治话语,从明太祖的口中传出,正是这一点以及相关的种种写法,让许多论者认为新历史小说的转型是狂欢的、后现代的以至于游戏化的。最后,《故乡相处流传》也处处弥漫着“可怀疑性”,曹操与袁绍闹翻的原因是“县城东街一个沈姓寡妇”,而千百年后,曹成、袁哨在迁徙途中又成了哥们,这使曹成感叹道:“历史从来都是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闹复杂了!”
四、想象历史:从虚无到自由
如上所述,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之“创伤书写”与“历史虚无”交织在一起,在历史的角落里,以怀疑的眼光审视包含血泪的史卷和充满苦难的国度。“‘否定既有的一切信念’是虚无主义者最为突出的标志”,某种程度上,新历史主义在“否定”之中完成了对古今伤痛的双向解构,而“历史虚无”恰恰是这种“解构”和“否定”的表面。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创伤书写”为内里,“历史虚无”为表征,似乎还是逃不出旧有的研究范式——游戏历史——的窠臼。然而,回顾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文学实践,将之归于“叙事游戏”,归于“商业规则和大众消遣读者的‘历史妄想症’的俘获物”,都或多或少忽略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文学根性和艺术张力,也忽略了作家的辛勤劳动和艺术创造。正像尼采固然高呼“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也提出“超人”的理念,“虽然说到底是虚妄,也要直面。要做超人!要有无穷的意志,永不止息地向上。”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即使是“游戏化”的历史叙事,即使是表现为历史虚无,却仍然表现出较为出色的文学艺术品性,清空了历史叙事、文学叙事障碍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往往展现出强烈的艺术想象魅力,给我们展现了一部部亦真亦幻的古今传奇。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中的叙述者生长在当代中国,却令想象的翅膀飞跃千年的历史长河,回到柔然的起点,追忆“母系”祖先的英雄史诗。而现实生活中的上海,琐碎的生活令叙述者感到庸碌和不耐烦。跟随叙述者的视角,读者的思绪可以向千年前历史的深处尽情伸展,通过追溯母姓“茹”氏的根源,在对柔然民族史的追忆中,草原上一段段英雄史诗就呈现出深厚的魅力。并且,古今的相互交织令叙述者完成了对庸碌“现实”和“父系”史观的超越,寻到了隐藏在历史长河之中传承不断的生命力和“草原精神”。显然,王安忆的《纪实和虚构》以一种“想象历史”的方式展开文本的叙事逻辑,文本内容不必完全符合文献记载,而且在叙述者的想象里,草原史诗具有摄人心魂的气概,叙述者也正在“想象历史”的过程中达到了超越庸碌现实的自由彼岸。
王小波《青铜时代》的三部长篇就极具想象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构建了历史的想象王国。长安城的意象贯穿《青铜时代》三个长篇,《红拂夜奔》里的长安城就是压抑人性、无趣的代表,风力长安、水力长安和人力长安三种城市构想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命运,皇帝最终选择了最无趣的“人力长安”;《寻找无双》中的长安城就更是一座“无智”、“反智”的牢笼;而“堪为王小波小说艺术集大成之作”的《万寿寺》则延续了这一脉络,主人公“薛嵩”是个“探索者”,薛嵩生活在一个毫无生气的长安城,“一早一晚,城市上空笼罩着灰色的雾,在这个地方买不到漂白布,最白的布买到手里,凑到眼前一看,就会发现它是灰的。”众所周知,“长安”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城市实体”和“文化意象”,它既代表了强汉盛唐无可匹敌的强盛国力,也代表了知识分子称颂、追忆的美好时代。举例而言,鲁迅就曾经计划写一部关于杨贵妃的长篇小说,但在来到西安之后,西安贫穷落后的现实打破了鲁迅的想象,长篇小说的计划也宣告流产。而王小波的《青铜时代》却首先完成了对“长安”的消解,如果依照旧有的研究范式,这无疑是游戏历史、虚无历史的实际证据,但是回归到“创伤书写”的核心,回归到“文学”艺术的审美特质,却能够发现其“想象历史”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自由和诗意的灵魂。
《万寿寺》的叙述者以失忆者的身份出现在开篇,他阅读自己的手稿,试图从手稿之中找到真正的自我,叙述者停留在“想象”中,文本中的薛嵩却将“叙述者”的多种想象一一“实践”,其间具有各种复杂的隐喻和寓言式写作,一个核心事件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写,进而拥有多种可能,比如“薛嵩抢亲”事件,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薛嵩行动非常狼狈,红线非常不满,“你难道连条正经绳子都没有吗?”“你真笨蛋——还敢吹牛说自己是色狼呢。”薛嵩感到很没有面子,闷闷不乐,性格发生很大了变化。紧接着在下一节中,叙述者提到了另一种说法,薛嵩在水边截住了红线,红线很配合,薛嵩找不到棍子,用拳头敲红线,她顺势装作晕了。叙述者在这之后狡猾地说:“自然,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薛嵩在树林里遇上了红线。”三种说法,各不相同,让读者实在无从凭信,对于这种不确定叙事,或者说 “后现代叙事”,相信很多喜爱传统小说的读者难以接受,叙事者在说些什么呢?叙事者想表达什么呢?事实上,“表达什么”恰恰不是作者的重点,从“薛嵩抢亲”的三种说法来分析,三种说法结果上都不美好,“虽然有种种不满,但也后悔莫及”,通过“抢亲”这件原始而富有浪漫色彩的事情,彰显了生活真实的庸俗无奈。之所以用眼花缭乱的说法来表达,恰恰是用想象力来解构“庸俗”,达到举重若轻,“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达到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状态”,从而发挥“无中生有的才能”,深得小说的“虚构之美。”尽管王小波认为写《万寿寺》的时候,叙事成了一种抒情,但问题是虚构的“凤凰寨”、“薛嵩”、“红线”和妓女,究竟会在现实的层面发挥怎样的作用呢?那么营造奇幻的想象王国,其背后的解脱逻辑又如何成立呢?作为沉重的历史背负者,读者跟随“叙述者”的脚步,将沉闷的历史重负摆脱,在“诗意”世界里实现对情感的抚慰,达到“轻逸”的境界。
在虚构和轻逸之中,人们终于可以对这段历史进行一番“举重若轻”,这正是文学艺术的另一种魅力,从不同角度透析就有不同的答案,新历史主义小说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历史话语霸权的反抗,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面对历史的无力感,以及伴随而生的虚无感,但是在这虚无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虚构、轻逸和解脱。也正是在“纪实和虚构”的重重叠叠之间,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回环往复之中,我们方可触摸“自由”,得以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压抑和无趣,也可以暂且搁置在“集体”之中流传的“创伤记忆”,从而缓解“面对历史重负的焦虑”。?
五、结语
综上所述,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伤书写”是重新审视其“历史虚无”表征的突破口,在古与今的交织杂糅之中,“创伤”也宣告消解,而历史虚无恰恰是以“创伤”的古今双向解构为基础生成的。并且,凭借着“想象历史”,新历史主义小说获得了“诗意的轻逸之美”,抵达了“自由彼岸”,超越了现实与历史的庸碌和痛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将“新历史主义小说”之转型视为唯恐避之不及的历史虚无主义,视为游戏文学的急就章,乃至视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恶作剧,恰恰是遮蔽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扎根于百年中国沉痛历史的文化语境,更是遮蔽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对一种真实的“创伤文学”、“治愈文学”的历史诉求。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1942、“三年自然灾害”,还有“十年文革”,不得不说,二十世纪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死亡”和“创伤”。另外,二十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技术的变革为“创伤记忆”在集体中的流通提供了条件,也为“创伤理论”和“创伤书写”提供了土壤。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伤书写”和“历史虚无”就有了必然性与合理性。
一个遗憾的事实是,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一代人的“疗愈”,完全赶不上市场经济大潮之下欲望袭来的浪潮,大众文化“汹涌澎湃”,网络文学“如火如荼”,消费狂欢“日以继夜”,蓦然回首,“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二十世纪已经是近二十年前的“旧世纪”,目下时代早已不需要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治愈,文学的抚慰功能早已被金钱、权力和消费狂欢所“代替”。故此,当下并不需要“历史创伤的双向解构”,也不需要“从虚无到自由”,反而需要一场深刻而彻底的理性反思,穿透历史的迷雾,找寻二十世纪“苦难之根”,批驳百年中国 “颓败之因”,惟其如此,“创伤书写”和“历史写作”方能融会贯通,既能够回应当下浮躁迷茫的社会文化,又能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历史抒写一首国族的“史诗”。
注释:
①对于这些不再涉及真正的历史题材、远离了“家族史”的传志文本结构、对历史素材任意地采撷抒写的小说群,最早应当是张清华在《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中论述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局限性,“没有始终把握住观念与历史、文本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它强调了文本及其叙事主体的作用,但又由于过于放纵的虚构而‘虚化’了这种作用,这使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很快便滑入了叙事游戏的空间,最终变成了商业规则和大众消遣读者的‘历史妄想症’的俘获物,从而最终消解了它的先锋性质”。见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载《钟山》,1998年第4期。
张对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批判奠定了后来学者的阐释和研究范式,路文彬则写了多篇论文对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局限之处加以批判,其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浸染了的后现代主义的成分,“对历史的欲望化书写, 使历史被简化成性与暴力的排泄物。”“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挤抑, 滋长了‘新历史主义’小说‘反民粹主义’的思想情绪,曾被誉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大众, 再也博得不了‘新历史主义’说家的崇敬之情。”而这一切都最终归于一种新的文学、历史与现实的态势:“历史与现实都不再是各自独立的世界,而是混交于一起呈现融合生长的状态。事实同虚构彻底无法分离。”见路文彬:《历史话语的消亡——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情怀》,载《文艺评论》,2002年第1期。
其他学者的论述也多沿袭这一研究范式而未能有更大的突破,举例如:张景超《改写历史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舒也《新历史小说:从突围到迷遁》、刘川鄂,王贵平《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解构及其限度》、李阳春,伍施乐《颠覆与消解的历史言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特征论》、蒋淑贤《非历史化:后现代语境下新小说的文本策略》等。
②舒也在《新历史小说:从突围到迷遁》中提到:“新历史小说在泼倒脏水的同时执意‘连婴儿也一同泼掉’,以致于在反传统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遁入了价值虚无主义的虚空。” 舒也:《新历史小说:从突围到迷遁》,《文艺研究》,1997第6期。
③张光芒著:《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5-98页。
④⑤参见陆扬:《创伤与文学》,《文艺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史鸣威
推荐阅读:短篇小说投稿论字和词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