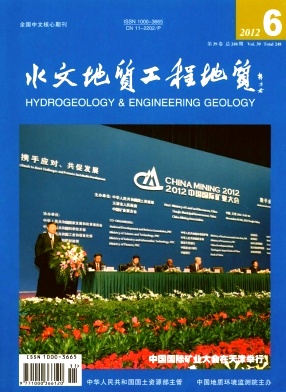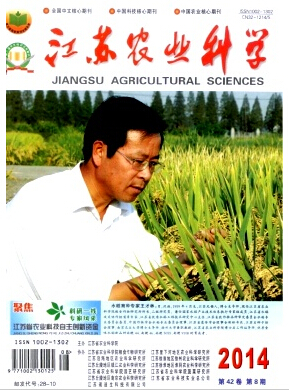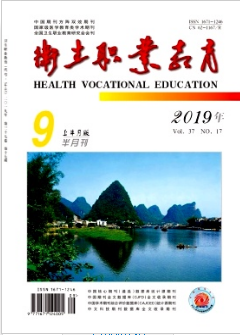《情采》:为情造文,要约写真

[摘要]《情采》是《文心雕龙》下半部的纲领,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阐述了文章写作中应遵循的创作规范。刘勰以“情”(质)指称文章中的个人感性情绪和理性思考,以“采”(文)指代声律辞藻等一众写作技巧,以及文辞的扼要精炼。具体来看,刘勰将文章写作划为三个层次,一曰“质文并重”,强调文章写作中内容、形式应相辅互济,不可有所偏废;二曰“先质后文”,昭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主张文采形式要为思想内容服务;三曰“为情造文”,申明思想内容应出乎真情,辞藻文采应恰当适度,并强调设立正确的规范来表达情感,使文章既有文采又突出思想情感,既为情造文又臻于文质彬彬。
[关键词]《文心雕龙·情采》;质文并重;先质后文;为情造文
综观《文心雕龙》50篇,只有《宗经》《情采》两篇针对所有文体从宏观上对内容与形式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就全书而论,《宗经》是基础,为全书确定了纲领,其中关于作文的核心主张——“六义”说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文章写做做出了总体要求。而《情采》则是下半部的纲领,所提出的“质文并重”“质而后文”“为情造文”等思想,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角度具体阐述了各体文章应遵循的创作规范,在源头上扶正固本,对当时及后世的文章写作理论都极具开拓和指导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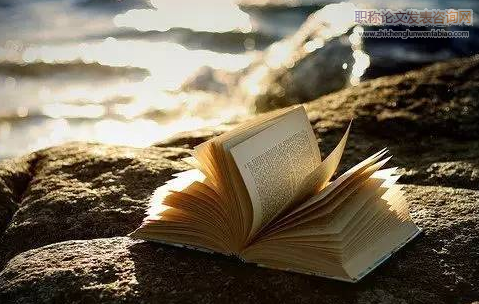
一、剖“情”析“采”
既然探讨《情采》篇,首先应该对“情采”一词辨析明确,否则一切论述都将是沙上建塔。在该篇中,“情”“采”分别各有所指。本文为便于表述和理解,依王志彬先生的观点,认为“情”“采”大致相当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但需指明,刘勰之“情”“采”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内容与形式”,更不是哲学命题中的“内容形式辩证关系”。只能说,“情”“采”蕴含一部分“内容”和“形式”的要素,与之相近但不相同。
具体来看,“情采”之“情”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既指蕴含人身五性的一己之情,又指理性层面的“情理”“情志”等。如《情采》所言之“志思蓄愤”“吟咏情性”等,是一己之情;“理定而后辞畅”“述志为本”“将欲明理”“心理愈翳”等,则是理性层面的志向或道理。刘勰如此广泛地界定“情”之范畴原因有二,其一,《文心雕龙》一书主旨为“言为文之用心”。刘勰之初衷是以此书指导当时各体文章写作的。因此《情采》所针对的绝非后世狭义的“文学”,并非单就诗赋而论,而是囊括诗赋、铭诔、奏议、书论等在内的众多文体,将有韵之文、无韵之笔尽数网罗在内。单以一己之情指代各种文章的内容,自是不够全面的。其二,《文心雕龙》全书立论根本在于“征圣”“宗经”。即以圣人之言、“五经”典籍为宗法对象。先秦时儒家所称的“情”“志”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并未如汉代以后将“情”“志”对立,以致“缘情”“言志”分道扬镳。因此刘勰所言之“情”,也是与“志”“理”合而论之的。
关于“情采”之“采”,也含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声律、对偶、辞藻、用事等文章辞采;二是指文章中蕴蓄的“秀气”。这里需对“辞采”“秀气”等略作辨析。在论述第一类“采”时,一些学者习惯表达为“有韵之文中的声律、对偶等”,这是欠妥的。刘勰所处之世,因辞采过分使用而导致的浅滥讹新绝不仅存在于“有韵之文”中,在“无韵之笔”中亦渐成风气。这也是《文心雕龙》在“文学自觉”的时代却仍持相对广义的文学观的原因。正因“矫讹翻浅”不止诗赋需要,各类文体都有必要,故而笔者认为在“声律、对偶”的表述中加入“辞藻”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将“采”仅局限于“有韵之文”的误会,也更合乎《文心雕龙》的语境。关于第二类所言之“秀气”,最早见于周振甫先生之说。但周译及往后持此说之学者对于“秀气”多是直译甚至不译,语焉不详,未有确解。笔者认为,周先生引《征圣》“精理为文,秀气成采”补充解释“情采”之“采”是允当的。而具体理解“秀气”应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首先,“秀气”的出处,即《征圣》篇赞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这里也是大致从内容形式两方面说明圣人之言的。此处之“文”并非是“文采”,而是圣人之文。译为“圣人的文章包蕴着精深的道理,以灵秀之气化作文采”。可知“秀气”是偏向于形式方面的。其次,鉴于《文心雕龙》是“子书型的文评”,虽分为具体的上下50篇,但是彼此并非相互割裂,而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应勾连全书以求他山之石。故笔者试以《风骨》之“骨”训于“秀气”。《风骨》篇的“骨”是对构辞的要求,针对“瘠义肥辞,繁杂失统”之弊提出,主张“结言端直”“捶字坚而难移”。刘勰在此表明对文采的要求不是简单的多或少,而是是否具备挺拔端直、精炼遒劲的“文骨”之美。这里也蕴含着作者因宗经而体现出的文学审美,即《征圣》中的“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以及《宗经》中的“辞约而旨丰”“酌雅而富言”“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等。第三,从《情采》本篇来看,亦可与上述观点相契。如“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再次提出了文章应具备“要言不烦”这一特质。因此笔者以为“秀气”确为“采”的一方面,大体指文辞方面的扼要精炼、典雅简明。综上可知,关于“情采”之“采”,应囊括两方面,一是声律、对偶、辞藻等辞采;二是蕴蓄于文章中的“挺拔秀气”。
另,某些学者依据“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一句,认为思想情感也属于“采”。持此说者将“形文五色”和“声文五音”与辞藻声律等关联起来,作为特指,与“五性”所代表的思想情感并为文章之“采”。但如此理解不免将此处的“文”范围缩小了。试想,文采包罗众多,就《文心雕龙》下篇提及的如“夸饰”“事类”“隐秀”“附会”等诸多“采”的具体内容而论,已非“五色”“五音”能道尽。而观上述原文,盖知此三者是总论确立文采之道,并非对文采的分类。笔者以为,理解这句话,首先要明晰“立文之道”的“文”所指为何。《原道》开篇即言明:“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本文综王元化、杨明、游志诚三位先生的解释,将此句译为“人文由来已久,很了不起,与天文、地文一起发生”。可知刘勰在《原道》中所论之“文”范围极广,囊括天地之文和人文。而《情采》篇所谓“立文之道”的“文”,是对《原道》中“人文”的进一步论述,从“形声情”三个角度阐述确立“人文”中一切文采的方法。“五色杂而成黼黻”,代表由加工色彩所构成的一切纹饰、事物;“五音比而成韶夏”,则言一切在人类文明下诞生的音乐;而“五情发而为辞章”,总述文章写作之道,铺垫“为情而造文”的作文主旨。最后刘勰认为,这一切人类文采的确立,都同天地之文一样,乃“神理之数”,自然而然。后文一切的论述,也是基于“情文辞章”所言。
综上所述,《情采》之“情”是指感性层面的一己之情和含蕴理性思考的义理、志向,大致相当于今人所谓的“文章内容”;“采”指的是声律辞藻用典对偶等写作技巧,以及文辞的扼要精炼,近于今天的“文章形式”。
二、文附质、质待文
刘勰在《情采》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质文并重”的观点: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渔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强调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质文兼备,相互依附,不然就难以存在。其中“质”相当于“情采”之“情”,“文”相当于“采”。“质文”之说出于孔子,是先秦儒家最核心的文学思想之一。《论语·雍也》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既体现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修身树德方面的要求,也为后世文学从内容形式两方面出发构建了一种文学审美观。孔子本人是极重视文学的功利性作用的,如《泰伯》篇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将文学与个人德行联系在了一起。又如《子路》篇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侧面反映出了文学应服务于政事的态度。及至《阳货》篇所说的“兴观群怨”,更是赋予文学以广泛的社会意义。这些都是在“质”的层面加以论述的,但孔子同时并不忽视文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写道:“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足见孔子对于文采的重视。汉儒整理的经文《仪礼·聘礼》也谈到:“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这是对先秦“文质”论的总结,也体现了汉儒的作文观,更是刘勰“质文并重”思想的直接来源。
若向更深处追溯,这种质文并重的思想还是中华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中和之美思想在文章写作层面的体现。《尚书·舜典》中的“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便是对“中和之美”的早期阐释;及至《论语》中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国语》中的“和实生物”,甚至于《老子》中所称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都表达了先民对于事物不偏不倚、阴阳中和的美学观的向往,成为中华民族本土哲学及美学的深层积淀。这一观念深深浸育着刘勰的文学思想,外化为其“文质并重”的作文观,也是《情采》篇中一切文学思想在哲学层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可是在刘勰所处时代前后,质文并重的文学思想却渐被忽略。晋宋之世,随着文学“自觉”意识不断发展,诗赋骈文及各类实用文体陷于华美,缺失了先秦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相对质朴的文风、真挚的情感,以及两汉经学强调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作用,一时间“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1]。刘勰作为一名传统士人,自幼得圣人“垂梦”,长怀“树德建言”“达于政事”之志,其文学审美以经文“六义”为本,因此对其时“采滥忽真,远弃风雅”的浮诡之作极为不满。这是他提出质文并重之作文观的现实背景之一。基于此,刘勰进一步阐明,文章写作在“质”的方面应“综述性灵,敷写器象”,抒发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对所描写事物进行铺叙陈说,使文章内容不流于空泛;在“文”的方面要“镂心鸟迹之中,织辞渔网之上”,对文辞也应加以雕琢,如此方能令文章彪炳后世,合于“文质彬彬”的为文正道。
刘勰提出文质观的另一现实背景是当时有一些论者虽反对浮艳文风却矫枉过正。如与他同时的裴子野从社会政治意义出发强调文章应“劝美惩恶”,却视“文采”为“雕虫之艺”“乱代之征”,一味推崇“四始六义”,将屈原以下之文章一概抹杀[2]。刘勰对此并不认同。《时序》篇中写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质文沿时,崇替在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风尚,不能囿于一时而不思进取。这是对裴氏等人所持复古保守观点的扶正。而在《情采》篇中,刘勰针对文采的运用更进行了深一步阐述: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
刘勰以先秦典籍为例指出,《孝经》教导人们在居丧期间不能说有文采的话,说明日常言语是带有文采的;《道德经》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而书中五千言又颇具辞采。可见文采不论对日常生活还是文章写作都是不可废弃的。
三、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情采》篇关于这一部分文学思想的论述相对精简集中,兹引原文于下:
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刘勰认为想要正确运用文采,需要具备相应的前提,即在作文之初能够辨明清浊,取舍正邪,故云“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这里的“择源泾渭,按辔邪正”,便是强调文章内容确立的重要性。在《文心雕龙》全书中,“邪”与“正”相对出现的次数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与“正”对举的是“奇”,如《正纬》“经正纬奇”、《辨骚》“酌奇而不失其贞(正)”、《定势》“执正以驭奇”“逐奇而失正”等等。所谓正,即圣人之道,经义所载;奇就是不符合圣人之道、经义所载的思想或表现方法。奇与变相关,因变而得奇。《离骚》有四事“异于经典”,但被给予“奇文”“伟辞”之赞誉,并明确表示要“变乎骚”,说明刘勰对奇、变的态度十分辩证,并非一概反对。不过求奇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即《通变》中的“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追求“奇”“变”一定要以“参古定法”为基本前提,也就是要“执正以驭奇”,牢记“酌奇而不失其贞”,否则恐怕就会步入“邪”路。“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刘勰认为《庄》《韩》“华实过乎淫侈”,以此强调要“按辔于邪正之路”。所以“邪”是“逐奇而失正”,完全背离了圣人之道、经义法度,是刘勰所极为不取的。
刘勰又云:“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认为女子真正的容貌美丽根植于“盼倩”,即其固有的风情姿态;而文章写作亦然,文学创作的成就高低不是由华美辞藻决定的,而是由其内容思想决定的。由此进一步确立了文章写作中“思想内容”的首要地位,这也是从文章写作角度对孔子所言之“素”进行了更为明晰的阐释。刘勰的文学、作文思想与“征圣”“宗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本段叙述中极为关键的“盼倩”一词即出于经典。《诗经·卫风·硕人》第二章写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极言庄姜出嫁时的美貌妆容。其中关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解释鉴赏,最早应推孔子及子夏。《论语·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从这段对话中似乎可知《硕人》最初的原文中在“美目盼兮”之后还有一句“素以为绚兮”。虽然已不可考,但孔子在言谈中阐发的相关文艺思想却是肯定的,即“绘事后素”,意为“绘事后于素”,要先有了素白的底稿,才能在上面用颜料作画。其理论内涵合于“文质彬彬”之论,同样是阐述“质文”之道,但剖析更为深入,明确了两者的先后层次,主张先“质”而后“文”。这一思想对刘勰影响是极大的,因此才有了《情采》篇中这一段专就作文而言的,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
基于上述认识,刘勰从理论层面总结道:“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理”是文章的经线,“辞采”是文章的纬线,只有使主体明确,内容雅正,文采才能润饰其中,畅行无阻。至此,刘勰正式阐明了文章写作中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强调文采形式要为思想内容服务。这是建立在“质文兼备”的基础上,既强调“先质后文”又不囿于一端以致偏废的辩证文艺思想,也就是“立文之本源”的真谛了。从思想渊源及现实意义来看,这既是对孔子“文质彬彬”“绘事后素”思想的综合与推进,也是对当时浮靡讹滥文风的纠偏与扶正。
四、为情而造文
在质文并重,先质后文的基础上,刘勰提出了文章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为情而造文: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作者以正反参照的写法对比了“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两种作文方式。所谓“为情而造文”,即是前文谈及“立文之道”时说的“五性发而为辞章”,强调文章的写作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心有所感,有感而发。如《诗经》的作者,从创作的发生阶段就先已“志思蓄愤”,有了充分的感情积淀,然后才发而为文辞,抒发自己的情感,来达到讽谏的目的。“为文而造情”则是指为写作而写作。作文之初衷并非心有所感,文章内容丝毫没有真情实意,所作之文也只是一味逞奇矜博,耀能炫技。需要稍做说明的是,此处的“志思蓄愤”显然脱胎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所借鉴的就是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之意。事实上这并不完全符合《诗经》的情况,司马迁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表达更有力度,刘勰也是以此为例,仅为阐明道理:先贤们在创作的发生、本体乃至功用各个方面都本着“为情而造文”的原则,始终有真实充沛的情感,所以才成就了经典。同样的道理,“以讽其上”只是借用,与刘勰本人的文学观并不完全等同。至于“诸子之徒”云云,也是就“为文造情”的现象而言,绝非对诸子的全盘否定。虽然也不妨尝试着“对号入座”一番,但其中行文需要的意义恐怕更大,作为系统严谨的作家论来看待恐怕有些不妥。
“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产生的结果当然不同,前者“要约而写真”,后者则“淫丽而烦滥”。由此刘勰又谈到了情之真伪问题,正面阐述如“要约而写真”,反面批驳则有“采滥忽真”“真宰弗存”,无一例外都体现了“贵真”“立诚”的要求。这是刘勰一贯主张的作文途径,他认为,所作之文只有出于真情,为情而作,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文章烦滥之弊,从而达到“文质彬彬”“理定辞畅”之境。与此相应,刘勰又提出了文章以“述志为本”:
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述志”即抒发性情之“真”、情志之“诚”。而强调其为“本”,实即在强调写“真”的同时不要忽略了“正”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刘勰的“情”“志”始终是建立在“道”“圣”“经”基础之上的,所以在《序志》中痛陈“离本弥甚”,在《宗经》中要“正末归本”。晋宋之代,不少“志深轩冕”“心缠几务”之辈,或为迎合风尚,或为干誉盗名,从而作些“泛咏皋壤”“虚述人外”的文章诗赋,致使“采滥忽真”之风日益显著,文坛之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几为一时顽疾。鉴于此,刘勰先是从宏观上正本清源,依“宗经”之法提出了“文质彬彬”以及“先质后文”的作文指归;进而从具体写作上彰明了作文方法:以为情造文,药淫哇锢习。
要求“为情而造文”并非不顾文采,“要约而写真”之“要约”就是对形式的要求。这就涉及文采表现的“度”的问题。刘勰说:
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
辞采的目的在于更充分地昭明情理,但假如过分浮华诡异,反倒会令情理受到遮蔽。就像过于精美的钓丝鱼饵反倒钓不到鱼一样,言语的意义也会被华丽的文采所掩盖。所以要在锦绣衣服外面加上一件罩衫,就是因为不愿过分装饰;而贲卦的文饰发展到顶点后又回到白色,可见还是以返本为贵。这段话一面引经据典,一面联系生活常识,反复强调的只有一个思想:文采的表现一定要适度。《宗经》“六义”中的“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也正是这方面的要求。因为情为文之经,文章以“述志为本”,所以文采一定要服从于情感表达的需要。
那么,应当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呢?刘勰接着言道:
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这也可以看作是刘勰对写作中处理好文质关系的总要求:要设立正确的规范来安排内容,拟定恰当的标准来表达思想。思想内容明确了然后再去考虑辞藻、声律等表现形式方面的元素,这才能既有文采又突出了思想情感,既为情造文,又做到了文质彬彬。至于正确的规范和恰当的标准,则当以《宗经》“六义”的前四条为指南:“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
《情采》篇中蕴蓄的有关文章写作的思想,即便时隔千载,今日看来仍极具现实指导意义与学术价值。具体来说,今人写作,“文不对体”“虚情假意”“浮词滥语”等弊病依旧不少。若依照《情采》提出的写作方法,则应“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明确所欲表达的思想内容,再据此选择恰当的表现方式。又如现今一些甚嚣尘上的所谓的“抒情美文”,多有无病呻吟、堆砌辞藻之作藏匿其中。观其文字或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致使“真宰弗存”“言与志反”;又或是“苟驰夸饰”“言隐荣华”,一味追求辞藻浮丽而导致文章冗芜,实可谓之“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对此,《情采》篇中所提倡的“为情而造文”“要约而写真”的作文指要仍不乏针砭之效,由此也更加彰显出《情采》篇所含文学思想对今天文章写作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作用。可以说,《情采》篇揭橥的文学思想不仅对齐梁时期浮浅淫丽的文风有补偏救弊之意义,更由此形成了较为完整全面的文章写作理论,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一种治学为文的有效原则和方法。
【 参 考 文 献 】
[1]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569.
[2]裴子野.雕虫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作者闫禾 石海光
《《情采》:为情造文,要约写真》
- 职称论文刊发主体资格的
- 政法论文浅析工会法主体
- 化学在初中教学中的情感
- 中学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方
- 法治论文投稿法治型市场
- 杂志社论文发表浅析推动
- 新疆教育报投稿浅析学生
- 分男女招生录取的合宪性
最新优质论文
- 论文转投是什么意思
- 科学管理研究是评职称认
- 论文发ei需要润色吗
- 经济全球化退与进论文发
- 安徽体育科技发表论文要
- 舞蹈的地域特征论文发表
- 医学论文投英文期刊怎么
- 水文水资源观测论文发表
论文发表问题热点
- 什么样的职称论文才能通
- 护理职称论文准备选题技
- 两会声音:解决基层医技
- 二级项目管理师评职资格
- 申报高级政工师发论文要
- SCI论文投稿状态有哪些各
- 工程造价师职称资格报考
- 哪里有2018中文核心期刊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