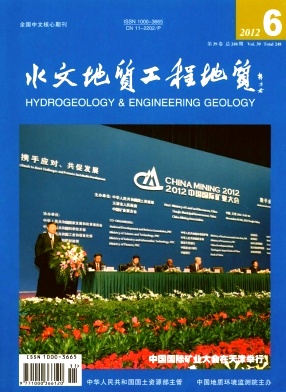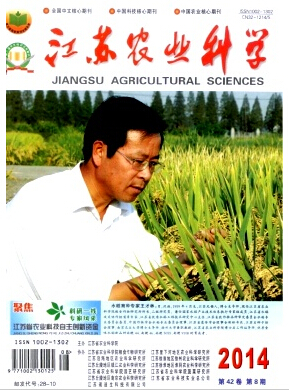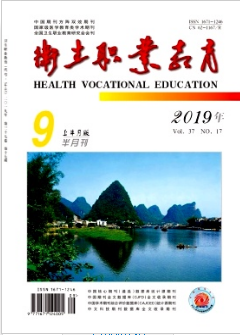“物妖”益増:明代时尚观念的兴起

明人尚风雅,尤以江南一带引领四方潮流。明中叶以来苏州习奢华,乐奇异,靡丽奇巧之物日有益增,营销至全国各地。好游历的王士性(1547—1598)敏感地捕捉到此不同于往昔的风气,以“物妖”之象述之: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人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杈,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而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
在今人看来姑苏城里这些竞买竞卖、流行如四方的物件着实迷人,但礼学之士王士性却称其为“物妖”,视其为败坏风化、危害社会的“俗蠹”。不仅如此,同一时期层出不穷的奇装异服等也被视为妖物,称为“服妖”,亦有样式新颖且价高的“墨妖”“扇妖”等['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流行的新奇物件感到不满的并非只有王士性一人,尤其是在政治中心京师、经济重心苏州两地,抨击抵制“物妖”之声不绝于耳。万德年以来,朝廷不得不频繁地颁布政令禁“物妖”,|3i然而屡禁不止=服饰器物贵重艳丽,且花样极多,大有一掷千金竞相购买者,士农工商皆投身于追逐“物妖”的洪流中,至晚明已弥漫至大江南北,势不可挡。礼学之士究竟将何物冠以“妖”之名,将物冠以“妖”之名又意味着什么?
一、"物带人号”:商业曰盛中的薄技小器
王士性所举“物妖”如“陆于匡之玉马”和“赵良璧之锻”是“物带人号”的提法。物前系其人者是古来用物的习惯之一,如孔明扇、韩君轻格(韩熙载制作的轻纱帽)、太师椅等,近日所制之物“亦以其字冠之,盖亦时尚使然”。古代流传后世的“无如苏子瞻、秦会之二人为著”,[41然古今好尚不同,明代好以工匠名字冠物,这就引起了礼学之士的不满:沈德符(1578-1642)论到将薄技小器冠以人名如同“南唐之天水碧”“近于妖谶矣”。151所谓“南唐之天水碧”是兴于南唐的浅碧色衣服。相传南唐后主李煜的妃子把没有染好的丝帛放在露天过夜,丝帛沾上露水竟起了变化,染出如同秋水一般的绿色。后来南唐人按照此法染色,并把这种绿色叫做“天水碧”,直到宋代,士女仍非常喜爱这种颜色。露水之“天水”与甘肃之“天水”谐音,宋人借此发挥以为天水是赵姓的郡望之地’南唐人着“天水碧”预示将被赵氏取而代之,“未几,为王师所克”,南唐灭亡:161“南唐之天水碧”在《宋史》论说灾异的《五行志》“服妖”一则中有明确记载。171明礼学之士以征兆国家治乱兴亡的“服妖”说论市面上追捧的流行物件,其用意不言自明。
不过,礼学之士的警世醒言似乎并没发挥功效,明中叶以降带有人号的物件与日倶增。如江南史料中记载有苏州的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安徽的吕爱山治金、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嘉兴的张鸣岐治铜炉,宜兴的时大彬治泥壶,江宁的伊莘野、仰寺川治扇等c|8i有关京师之地的史料中出现的则是一串北方工匠的名字,刘侗(1593-1636)撰写的《帝京景物略》可见。尽管被议为“物妖”,但无论如何这些名字都是一种影响力的存在。袁宏道(1568-1610)对“薄技小器皆得著名”的好尚有淸醒的认识,他一方面站在世风道德的立场斥责吴人为始作俑者:“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值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于吴中狷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资,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另一方面他从造物艺术的角度充分肯定时下流行的物件:“然其器实精良,他丄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9]明代文人对于工匠的肯定与欣赏不仅表在言论上,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交友往来。在美谈造物的过程中,文人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工匠造物,大大提升了造物格调。长此以往,这些原本社会地位并不高的手工匠人不仅与文人唱和酬作,还凭一技之长成为“与缙绅坐者”(王士贞《觚不觚录》)。
由此“物带人号”也就成为品位、地位、财富的象征。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勃兴,原本只在极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手中流传的“物带人号”一类的贵重稀有物件,成为富贵人家的常见摆设。手握金钱的商人穿着打扮、建屋造园、置办家具皆不惜成本,他们的财富扩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消费热情高涨。在市场上获得的成功令商人自信,他们开始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从商人阶层向士绅阶层的转换。在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上尽力模仿士绅是他们身份转换的门径,因此精巧雅致的物件成为商人必购的商品。然而,商人的文化水平和鉴赏能力远不及士绅和文人,这时“物带人号”的惯例便为他们攀登身份等级提供了便利—如同商标认证一般,成为购买高质量物品的快捷方式:
实际上,“这些名字已经变得相当程序化,人_们常常把他们搞混:一个世纪前,王世贞(1526—1590)将制造梳子的匠人赵良璧当作最好的锡匠;一二十年后的顾炎武又夸赞他打造的刀刃天下第一。”m当然,现存的明代锡器也好,刀刃也罢,没有一件我们可以确定是赵良璧的作品。至于明人是否能确定市场上的“赵良璧之锻”真的出自其人之手,恐怕也是难以保证的=当商人们抱着商业冲动投身文化活动中,资本的注入推动了手工艺市场的繁荣,在商业利益的刺激下百工数量增加,行业竞争愈发激烈,“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从业者“炫奇而贾智”,所制器物巧几于淫,M催生出“令人真赝难辨”的奢侈品市场。在这个奢侈品市场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高超的鉴赏能力,但只要拥有一件带有人号的手工制品,就可以说明拥有者所具备的财力和品位。由此来看,“物带人号”区分着市场上手工制品的优劣贵贱,同时区分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身份。
议论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将事实真相呈现出来:王士性等人将“赵良璧之锡”等视为“物妖”并非因为“物带人号”的惯例本身,而是因为明人好尚—将历代视为薄技小器的手工制品冠以工匠之名。而将带有工匠之名的手工制品被视作“物妖”,并非因为物件本身的精巧雅致,而是因为价高相售、竞买竞卖、四方流行、奇技淫巧令人真赝难辨。追踪到底,赏玩之物被冠以“妖”名的根源在于它是商人转换社会身份的需要。换言之,“物带人号”在商人社会身份的转换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引起礼学之士的注意。如果说王士性所论“物妖”只是在贵重物品领域,只有拥有大量金钱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购买和收藏=那么,在商品经济氛围中不断变化的日常服饰—“服妖”则在更广泛的层面揭开了“妖”物的神秘面纱。
二、奇装异服:奢靡之风释放的“服妖”
明京师的街头巷尾有不少新奇的物件,有一些还是异域风情,如摺扇、高丽纸、高丽墨等。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行走的物件服饰c成化年间,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等,[n]国都里“自带以下,拥肿如瓮,匍匐而行”(《谷山笔塵》)的朝鲜使臣甚为抢眼。时人品头论足,以为蓬蓬张起的衣服甚是奇异,仔细询问观察才得知,秘密在于朝鲜人在腰间系的裙子。这种裙子的织造材料、工艺和审美不同于“中国服”,以有硬度且细长的马尾织造而成,裙子有自然膨胀之态,如同一把撑开来的伞。朝鲜人称之为駿裙,明人又称之为马尾裙,发裙或驁裙。1131
马尾裙于成化年初流入京师,当时只见富商大贾、贵族子弟和妓女穿着,“体肥者一裙,瘦者削者或二三,使外衣之张,俨若一伞,以相夸耀”(《寓圃杂记》)。不久之后,朝廷的内阁大臣万安四季不离马尾裙,以为蓬蓬之态“取观美耳”=朝中官员竞相仿效,甚至“素以理学自命”的礼部尚书周洪谟为了使蓬蓬张起的效果更加明显,在腰间系两条马尾裙=年轻的侯爷驸马们还对裙子进行改造,在裙内绷上弓弦使其蓬起之态整齐美观,可谓煞费苦心。成化末年,极目朝中上下,只有吏部右侍郎黎淳一人不服马尾裙而已。在满朝文武大臣的推动下,马尾裙的来源从进口变为自产,出现了专门定制马尾裙的成衣铺,一时间京师着马尾裙蔚然成风。毕竟是国都重地,朝廷官员、贵族公子、商贾富人、青楼歌妓同着一服,竞相夸耀,渐招致不满。礼学之士以“无贵贱用之”“废夏而尚彝”皆“非制”,将马尾裙视为“服妖”。弘治初年朝廷下令禁止服马尾裙:“今后有用马尾服饰者,令锦衣卫缉捕,余皆泛言不允。”(《大明孝宗敬皇帝实录》)
尽管后来马尾裙不禁而制绝,但此新奇夸张的裙子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风行已经严重挑战和冲击了“望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的等级秩序。逐渐地,明中后期的人们普遍感觉到,从一个人的衣着装扮来判断他的社会地位在很多时候已经变得靠不住了。事实也是如此,在物质财富的刺激下“兵民服色器用,已有定制,近在京多犯越”,“服用则僭大红织罗缎遍地金锦,骑坐则僭描金鞍轱减银鞦辔;首饰则僭宝石珠翠。”(《明宪宗实录》)风俗尚奢,无论贵贱,时人对于僭越行为“括不为异”,朝廷不得不命巡按御史,督同府州县掌印官严加禁约,对于违式[141服饰者,依律问罪,对于徇情不举者,一并追究。1151然而,禁令未有成效。“官民服食,倶无限制”(《张文忠公全集?陈六事疏》)。庶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向达官贵族看齐,一度“四方丝贵金少”。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费用习以为常”,织造异色花样,造违式房屋,居室雕画,首饰滥用金银,“娼优下贱以绫缎为袴,市井光棍以锦绣续韈,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蒙朝廷禁止之诏下而民间僭用之俗自如。”?
推荐阅读:服装类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
僭越之风竞起,违礼逾制已成风俗,“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万历《通州志》)的淳朴民风一去不返。庶民百姓即便是经济上不富裕,也要充门面,借贷享乐,以致“服妖”盛行。无论是头上的衣冠,还是脚下的鞋履,形制变动不居,样式翻新的周期越来越短,用料贵重奢侈,色彩艳丽夺目。服饰不再只是满足于遮蔽身体的基本要求,礼制与习俗也不再那么重要,人们主动追新求异,满足感官享受,“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求及远方吴紬、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折,倏忽变异,号为时样,此所谓服妖也。”[171
京师不仅要从富庶的苏吴地区采购面料,样式品位也向苏吴靠拢。苏吴地区服饰变化快、流行周期短是其他地方所不及的。就妇女服饰而言,“大率五年乃克周遍,所始之地厌弃已久,所效之±纏仿方新”,间周边的浙江人也极力模仿苏州所尚,如忽大忽小的袍袖,忽高忽低的巾帻,但是当浙江人仿效时,苏州人袍袖又变小,巾帻又变低了,苏州人就以“赶不着”笑浙江人〇1,91尽管浙江人在服饰创新上总是略逊一筹,但是不畏礼制,不忌习俗的态度并不比苏州人弱。一位生活在万历年间名叫徐曾唯(生卒不详)的士子记录了家乡余姚县城里男子巾式的变化,短短几年竟有几十种。如有“缀玉、结玉瓶及上有覆以前后响板,云前后五七折叶”等,由于之前从未见过此等样式,不知如何称呼,更为不解的是,竟然还有人不顾忌讳佩戴绿色巾。徐曾唯对此颇为愤怒,叹曰“岂不为服之妖乎。”120]
苏吴地区衣食住行不仅追求变化,更重要的是追求高品质:“衣裳冠履未敝而履易;饮食宴会已美而求精;衣则忽长忽短,袖则忽大忽小;冠则忽低忽高,履则忽锐忽广。造作者以新式诱人,游荡者以巧冶成习,富室贵宦自堆箧盈箱,不惜纨扇之弃之矣。”12”可见,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尚俭禁奢的用物道德要求早被苏州人抛之脑后,“物”的美观、精致与独特才是他们的追求。当时苏吴地区的生活风格被称为“苏意”或“苏样”,以肯定其在引领社会风尚中所处的先锋地位c[221
从京师的崇艳好异到苏州的雅素相高,无论大俗还是大雅,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追逐风尚的潮流中不仅有士绅富商也有文武百官,庞大的庶民百姓群体对此也怀有极大的热情。尽管礼学之士一再抨击抵制奢靡无度,感慨悲悯尊卑无别,将奇巧多变、靡丽奢华的服饰器物冠以“妖”之名,但是“物妖”盛行已是大势所趋,正如吕坤(1536-1618)所言“势之所在,天地圣人不能违也。势来时即摧之未必遽坏,势去时即挽之未必能回。”[23丨
三、“物妖”与时尚
明代礼学之士所谓的“物妖”,不过是以新、奇、少、艳为主要特征的日用之物和赏玩之物。在商业日盛的明代,尤其是明中晚期以来日尚奢靡,“物妖”所建立起来的美学观念引导着明朝社会追捧式地接受、盲目地消费某种风格或品位的“物”。想来今人对古代的“物妖”所表现出的特征并不陌生:新奇,物品为变化而变化,呈现出物欲的彰显;竞买竞卖,物品凝聚着富商贵人的炫耀性消费,是社会等级差异的宣示;爆发式流行,由首倡者引发一场群起仿效的态势,物品一时间倍受追捧,而翻新速度又导致其在短时间内被人遗弃。总之,昂贵的商品不断被出售,同时有更多的人能买得起价格更高的商品,人们不停地买买买,物品不停地变变变,“物妖”以京师和苏州为中心弥漫四方。而这正是人们追求时尚的完美构成,换言之“物妖”盛行成为明代时尚观念兴起的表征。那些“美”“艳”“奇”“巧”“媚”“异”的时尚物件,用“妖”字来描述其外在的感官效果再合适不过。当敦厚俭朴的世风转向浮靡奢侈,最终汇聚成一股僭越违礼的浪潮气势汹涌地奔向朝野上下湮没全国时,对于那些从物中不断满足消费冲动、获得享乐欲望的人而言,“妖”字极为生动地显露了他们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的状态,是一种“诱惑的美学”丨241的呈现。但是,“物妖”一词毕竟出自逆奢靡之风而行的礼学之士之口,是王士性比做“俗蠹”的一类。
同王士性一样,仁和(今杭州)的张瀚(1510-1593)对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引领四方风尚有详细记载。他在描述“人情皆观赴焉”的江南之景时,并未表现出作为江南人的自豪情感,反倒是担忧习奢华、乐奇异的风俗:“盖人情自俭而趋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俭也难。今以浮靡之后,而欲回朴茂之初,胡可得也?”岡不难看出,张激的担忧里还夹杂着对明初淳朴风格的追忆与怀念。礼学之士饱受礼制文化的浸淫,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他们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的捍卫者,这在常理之中。然而,旧制度失其权威,新制度尚未确定,在此过渡时代,人皆徘徊歧路之时,礼学之士无可奈何、焦虑不安、留恋怀旧之情溢于言表,也是人之常情。顾起元(1565—1628)叹曰:“嗟乎!使志五行者,而有征于服妖也。折上之巾,露卯之屐,动关休咎,今之巾履,将何如哉!,’岡李乐(1532—1568)论道:“厌常喜新,去朴从艳,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在富贵中人之家,且犹不可,况下此而赋役长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香二三百里内,自丁酉至丁末,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打雷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此乱象也未几成戊申,自昆陵以南洪水骤溢,米价腾涌。插秧田十无一二,冬必不获。明年己酉,不知荒歉作何状?既荒,恐有意外不测之变,奈之何哉!”1271礼学之士愿意相信“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礼记?中庸》)也愿意用汉儒提出的“服妖说”来警醒世人。在李乐等人看来,明人追捧的靡丽奢华的生活方式,流行的浓妆艳质的装扮即是为乱象,预示着国家不安。将自然灾害、人事变迁附会于物,不免隐含着他们身处变动社会的不安和恐惧。在这里,“妖”字明确了他们对物欲诱惑的警惕,进一步而言是对时尚的抵制。
由此来看,“物妖”的盛行恰恰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时尚的发生。时尚是商人借此用来挑战等级权威和社会名流的工具之一,它作为社会身份转换的手段发展起来,通过世人竞相仿效促进自身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时尚撼动了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反过来说,在等级秩序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时尚是不可能发生。明初承汉制,上下皆须遵照身份等级用物,“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汉书?成帝纪》)c明太祖按照身份等级规定房舍、服饰、车舆、器用等各方面的礼制,网目不疏,不仅有庶民之别,百官自一品至九品所遵用物规定也各有不同。如若违式或违禁,将受到法律惩处。严谨的制度和严苛的政令匡正各有等差的社会秩序,维持淳朴守分、敦厚有礼的社会风俗。如此以来,“器以载礼”的服饰器物受到规训,造物无法呈现为变化而变化的逻辑,“物妖”说鲜有。但是,明中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礼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以致“礼仪不行”,僭越违礼时有发生,“物妖”得以释放。更为重要的是商业日盛激发了压抑和禁锢已久的消费冲动与享乐欲望,享用新奇华丽、雅致精巧的服饰器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物妖”盛行势不可挡=明朝社会发生的变动令礼学之士焦虑不安,甚至感到恐惧=“物”作为社会生活最为直观和形象的体现,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的变化—礼学之士“借物抒情”,将物冠以“妖”之名: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物妖”盛行也映射出时尚观念兴起在明代的社会意义。
结语
王士性等人将人造之物冠以“妖”之名,可追溯到两汉时期“服妖”的提法=“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两汉“服妖”说源于灾异思想,其产生不免受到神秘的、非理性的因素左右,但说“物妖”者的意图并不神秘,与“物妖”相关的政治行为、制度安排并非取决于神秘因素,而是现实的思想、习惯和政治需要的产物。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凡是不符合自身性别、地位和所处场合的用物均有可能被视为“物妖”,将其与国家动乱或人事变迁相联系。古人云“事出反常必有妖”,“物妖”的反常无疑是指与儒家礼制和习俗对立的状态。借助五行灾异思想打压反常之物以框定和维持社会秩序,是国家层面的心态;用反常之物人的心态却是百态的’这是自“物妖”说提出之初就表现出的迹象=但无论如何,某物一旦被冠以“妖”之名必然难逃被抵制打压的命运。然而,明中叶以来“物妖”益増且呈盛行之势。对此,与其是说是物从礼制文化的规训中得到自由,不如说是用物之人有冲破等级秩序之藩篱的勇气。而明人勇气勃发与明代社会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尤其是与商品经济勃兴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反映有莫大的关系。
进一步而言,“物妖”概念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太多的隐喻观念。我们从特征、功能,还有社会态度和社会效应等方面考察“物妖”,借助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时代信息,挖掘它与时尚之间的关联,将其视为时尚观念的表征,并不是将其与时尚混谈为同一概念。关于“时尚”,一般说来是“具有一定之规的系统变化的逻辑”,1281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造物技术,乃至是阶级、性别、地域等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时尚”的阐释是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本文以古已有之的“物妖”为切入点,探讨的仅是时尚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兴起的一项命题。
有意思的是,在明朝灭亡二百七十四年后,正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洗礼的近代中国,仍然有相同的概念出现,而且还刊登在了民国《时报》上,名为《取缔妇女妖服之呈请》。此文是一位上海议员致江苏省公署的建言,他所谓“不成体统,不堪寓目”的“妖sr,即“女衫手臂则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至一尺有余,及至暑天,内则穿一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纱之衫纱,几至肌肉尽露”的服饰。1291很显然,这位议员对女性显露身体不胜惊异=恐怕他万万想不到,转眼光阴,上海的女影星们脚蹬高跟鞋,衣装紧透,描眉画眼,美容塑形,拍摄泳装照迅速掀起一股时髦的现代风尚。上海顺势成为摩登之都,女性以身体制造时尚,以身体推广时尚,并由身体来穿戴时尚演绎民国的时代风景:欣然,这位“明礼知耻”的上海议员递交的请呈,为本文所探讨的话题作了一个接续两百年的注脚。
《“物妖”益増:明代时尚观念的兴起》
- 职称论文刊发主体资格的
- 政法论文浅析工会法主体
- 化学在初中教学中的情感
- 中学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方
- 法治论文投稿法治型市场
- 杂志社论文发表浅析推动
- 新疆教育报投稿浅析学生
- 分男女招生录取的合宪性
最新优质论文
- 经济全球化退与进论文发
- 医学论文投英文期刊怎么
- 水文水资源观测论文发表
- 安徽体育科技发表论文要
- 论文转投是什么意思
- 舞蹈的地域特征论文发表
- 论文发ei需要润色吗
- 科学管理研究是评职称认